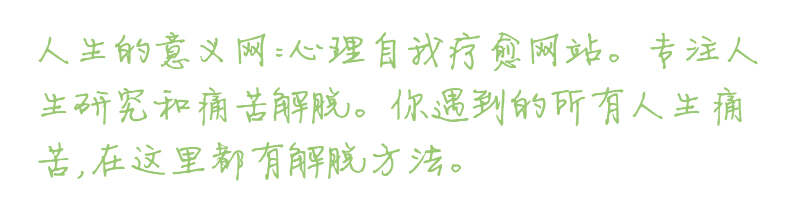我就是那四成认为人生没有意义的北大新生之一
2016-11-28 09:52:33 发布:人生的意义网

北大入学第一周,学校要求我们做一个心理健康测试。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一边做题,一边和室友开玩笑:按这个题目设计的思路,我肯定是抑郁症无疑了。
北大新生心理健康测试里正有一题,你认为人生有意义吗?
按照有无程度,有ABCD四个选项供我选择。
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毫无意义。
至于什么“你最近很难过吗”之类的题,因为正处于一段感情的断层期,我只好老实选择了最严重的那项。
就连“你有过结束生命的念头吗?”我也诚实地答了“偶尔有”。
我应该就是最近流传颇广的那篇文章《北大四成新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甚至已经放弃自己!》里40%的一个分子。
那篇文章的开头说:
一个现象近年来越来越突出——
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没有明显创伤,生活优渥、个人条件优越,却感到内心空洞,找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就像漂泊在茫茫大海上的孤岛一样,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甚至找不到自己。
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我现在活着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这样活下去而已,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
(选自《北大四成新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甚至已经放弃自己!》开头)
怪不得文章里个案那哥们说精神病医生很傻逼,我也觉得。虽然我完全知道如何在心理健康测试里答出非常健康的选项,但出于一种惯性的诚实原则,我还是答出了一个抑郁症倾向的结果。嗯,报告结果显示我有严重的抑郁症倾向。
如果再严重一个等级感觉会被约谈。
我知道自己可能有点变态,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有抑郁倾向。
毕竟任何一个以正常寿命而终的人可能都会惊讶地发现,他这一生,曾经轻率地动过数十次乃至数百次自杀的念头,甚至冲动地实施过数次自杀的准备,然而他还是活到了寿终正寝的那一刻。
这个社会最苛刻的一点,莫过于对正常的标准定义实在太狭隘。
文章里面反复提到这个数据:
我做过一个统计,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请注意这是高考战场上,千军万马杀出来的赢家。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我现在活着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这样活下去而已,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
所以我们回到一个非常终极的问题,人为什么要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他们这种情况并不是刚刚产生的,他们会告诉我,我从初中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疑惑了,直到现在我才做了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传统的西方的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对他们都没有效果。
……有一个理工科的优秀博士生,在博士二年级时完成了研究,达到了博士水平,这是他导师告诉我的,他屡次三番尝试放弃自己的生命。他当时两次住院,用了所有的药物,所有电抽搐的治疗方法。出院时,我问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他说精神科医生很幼稚,可笑。我表现开心一点,他们以为我抑郁就好了。
要讲的是,他不是普通的抑郁症,是非常严重的新情况,我把它叫做‘空心病’。
我从十四岁那年开始疑惑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其实这本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伴随了我整个青春期,于是高考结束后我选择了哲学系,念了最冷门的宗教学。我觉得这两个专业大概会给我答案。
意义的缺失带给一个年轻人的恐慌,茫然与无所适从,确实是一件足够沉重的事。所幸的是,在本科毕业之后,我对于人生没有意义这件事已经开开心心地接受了。
哲学家们到了最后,都会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是虚无的。或者说,从语义学的角度讲,“意义”这个词所承载的重量,是任何文字都无法承载的。而不同的宗教,无非都是一套封闭的世界观,你通过赞同某些前提,来换取一个安全的有限自由的大牢笼。
人类是伟大的,我们终结了自然的无序状态。为了生存和更好地生存,世世代代的人都在试图为自然立法。我们没有因为自然的无序而恐惧,或许我们通过生命的传递与更迭而克服了这种恐惧,我们创造了科学,创造了伦理,创造了政治,创造了生活。
然而个体的生命是卑微的,维系我们生命的,或许是爱,是因果,是命运,或许是莫名其妙的责任,是基因里被写入的生存欲望,唯独不是意义。
意义这个词太重了,配不上人生。
我们生来就不自由,不平等,却还要再戴上意义这个枷锁。
“否定了人生的意义”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你如何去否定一个不先验存在的东西呢?
所有的意义,都是被建构出来的。而需要被建构才能出来的东西,又怎么可能是必需品?
你一定会觉得我这些想法很偏激,如果你也思考过这种问题,那么请问你,发现人生意义虚无的一面是不是非常容易?
反正比发现有意义的一面容易多了。。
而从对自身生命体的内观开始,到对世界和宇宙展开思索的人,当然也有更容易会对其他知识和奥秘产生兴趣。
回头想想,那些从十来岁就开始思考这种问题的人,上好学校的概率是不是更高一些?
如此一来,在一个不错的学校里,有四成的新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好像也不是一件多么可怕到无法理解的事。
安徒生写过一个童话,里面有一个虚荣自负的小姑娘和一双永远无法停止跳舞的红舞鞋。
有时候我觉得思考就是那双红舞鞋。
一旦你开始思考,就将面临被思考主宰的人生。
虽然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即使很多人都悲哀地听说思考的尽头是虚无主义,但穿上了红舞鞋,就得毕生去跳舞。
前天早上在院群里看到老师和同学转那篇文章讨论,今天又看到很多人在转这篇文章,落脚点不过在痛斥教育的虚伪和学生的虚弱。
(我们的教育必然是有问题的……这个就不讨论不反驳了)
然而,我并不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认为人生没有意义就是有病。
你可以勉强说是时代病,因为在历史的循环里可以看到这个病的轮回。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立国的艰辛,没有像老一辈人那样有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共同记忆,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全部建构主要来源于政治课本和新闻联播,所以无法把个人价值溯源完全植根到宏大叙事里。
我们的成长时期,注定了我们没有机会吃上太多苦。罗列一下同龄人中最痛苦的几件事,要么是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从而被攀比折磨到晦涩,要么是考试结果比想象中低了一些从而错过了不错的机会,要么是原生家庭有或多或少的毛病从而拿来当做性格缺陷的借口,要么是像过家家一样投入到一段感情然后在失恋之后自怜自艾自暴自弃。
确实,这些痛苦,在经历过实打实的饥饿、家徒四壁、亲情淡漠以及不公待遇的上一代人眼中,就是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证据,“一点点小风浪都禁不住”、“矫情”、“抗打击能力弱”等词都顺理成章地脱口而出。
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苦。他们羡慕我们,我们也羡慕他们。
我们这一代人的父辈,虽然早年艰辛,但赶上了可能是国家开口最大的一次上升通道。估计等到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不过留下几个狭窄的象征性出口。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卷入的世界互联网革命,无疑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两次机会。
而社会流通的途径窄化与硬化,最难过与绝望的莫过于通过高等教育体系进入到高校的平民子弟。
之前被刷屏的两篇文章,显示的就是这种恐慌。一篇是人大同学写的《非典型985毕业生的大学简史》、另一篇是复旦同学写的《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当时看得我三天没刷朋友圈。
人大和复旦都是站在中国高等教育制度金字塔的学校,这就会给人一种错觉:觉得自己经过千辛万苦和一批人考到了同一个不错的学校,就是通过个人努力和同学们站到了同一个新的起跑线上。
每次上公共大课的时候,屋子里乌泱泱能坐满三四百个人,都难免令人遐想。难道我们真的要天真地以为我们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吗?
有些人是随便考考就坐到这里的,有些人是一天48小时拼上来的;有些人一年旅游好几趟,从小学开始每年暑假都去国外参加名校夏令营,而有些人到过最远的地方不过是来北京上学;有些人的家庭已经为他们铺好了一条锦绣前程,而有些人毕业之后的目标是先还完助学贷款。
这种由命运择定的不平等,被我们坐在同一个教室的假相暂时性地蒙蔽了,但一旦离开学校,离开这个精致的囚笼,立马就会以十倍百倍的差距显现出来。
很多人没办法接受这个现实,你的同学,其实从头到尾都不是和你一个阶级的人。
如果放三十年前也就算了。
但这个年代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早早地通过大众传媒和社交网络窥视到了阶级的鸿沟。没看过的生活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念想,而“看到过的生活”却是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的折磨。
所以我们越来越浮躁,越来越不甘,越来越有挫败感。
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世界,经历过市场经济的洗礼,进入了一个彻底的伦理碎片时代,被裹挟着卷入信息爆炸的洪流中。这种痛苦,是成长早期远离信息时代的上一代人无法理解的。
个人主义的彰显,确实是时代的进步。
从集体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个体,有了更大的自由,更大的做梦的余地,却也有了更深的孤独感。
最显著的就是旧式伦理被打碎后,新型伦理尚在形成过程中,我们正在失去一个绝对的政治正确生活方式,无法适从这种伦理碎片。我们接纳了越来越多的以前与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的观点,比如同性恋、不生孩子、女权、对婚姻和家庭的自由态度等等,我们努力抛弃长辈们灌输给我们的“什么是最好的生活”,但又没办法支撑自己立马找到一个立足点,所以在摇摆之后要么退回到安全圈,要么选择一个随机数——反正这个社会可以为所有的选择提供自欺欺人的辩护。
上半年随笔集出版时,我说我写作的最大动力就是慢慢地发现:原来我们都一样啊,一样经历着青春的困顿,一样面临着初尝爱情的张皇,一样承受着时代变迁的失落,生存在理想国与动物城的夹缝里,从而在社会规范与自我价值的两极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仰望自己金光闪闪的未来,有时候却惊惧自己将一事无成。
一样都解构了人生的意义。
这注定是一场冒险。这意味着你走在人生的路上,你看到的前方永远是一片雾茫茫,而大雾掩盖的地面,可能就是你看不见的悬崖断壁。
只要是个人,就会怕,会腿抖,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你明明知道,只要放出一个意义的技能,前面就将烟消雾散,困局迎刃而解,却仍然要固执地迎着大雾走下去。
将意义作为人生的支柱与前行的动力,是很好的生活方式;
但没有意义的人生,怎么就不可以是另一种生活了呢?
前者要面临意义废失的风险,很有可能前半生追求的意义到了某一天,就轰然倒塌——一个人要容忍自己的一生被意义定义,其实需要更坚忍的精神,并坚持不懈地终生给自己洗脑;
后者要面临的不过是意义缺失的恐慌,而这种恐慌迟早是会被克服的,要么以生命的主动终结克服,要么就忍受巨大的不确定性去继续生活,直到习惯了思想的漂泊。而对于后一种选择,罗曼罗兰早就说过了:“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了生活,然后继续爱它。”
作为人类的整体,我们有长久的生命去给自然立法,恐慌会被悠远的DDL稀释;但作为自我的个体,我们只有一辈子的时间给自我立法,意义不该是唯一之法。
然而我们得以度过一生的,穿越那些焦虑、崩溃、恐惧的仰仗,无非是从历史和经验中得出的绝对禁令、社会训导规范的所谓体面,和与直觉相关的情感冲动。
理性是人类后天的训练成果,不是本能;意义是群体为之构筑的原始堡垒,不是必需品。
踏踏实实迈上一条虚无之路,是无奈,也是自我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