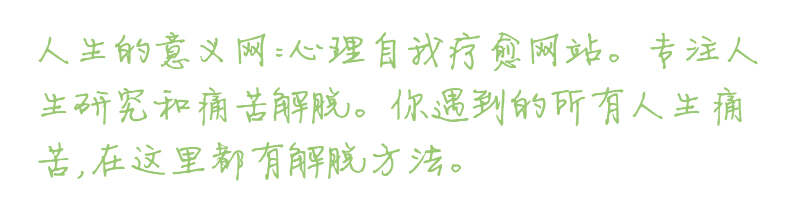三和大神:生活在魔幻现实主义里的特殊人类(二)

三和人力资源市场

三和的传奇人物:红姐
一个人需要放弃些什么,才能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深圳三和人力市场附近,有一群人几乎放弃了一切,打造了一处黑色桃花源。这些被称作“三和大神”的打工者,放弃了家庭、生计和一切社会关系,甚至卖掉了身份证件,只愿沉溺在网络游戏当中——他们是当今最“废”、最“自由”的年轻人。
2017年夏,故事硬核作者杜强在三和实地体验一个多月,通过传奇人物红姐的故事,展现了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世界。
精神鸭
在三和人力市场的拐角处,石头大哥四仰八叉地坐在轮椅上,他腿部以下没知觉,可模样看起来只像是走累了、顺手找地方歇歇脚。每当有人从身边经过,他便像摊开扑克牌一样拿出十几张籍贯各异的身份证,一边兜售,一边评判起各省人民的道德水平和小姐的质量。
卖给我一张证件后,他开始指点迷津,年轻人,我看你长得还可以,要不要去做鸭?见我犹豫不决,又教授门路,“只跟富婆聊聊天也可以,嘴巴甜一点,忽悠得她神魂颠倒。”
“那就是谈恋爱啊。”我说。
“太俗了,就是精神鸭,那才是赚大钱的。”他正赌着码,右手颤巍巍地挡着手机屏,好让开奖数字挨个显现。“深圳是个空虚的城市,懂吗,那些人空虚,所以你有钱赚。”
说话时,附近的廉价网吧和饭馆刚刚点亮了招牌,灯光照射下,打工仔、赌徒、酒鬼和出卖身体的男小姐聚集在街巷里,一脸萎靡的神情。龙华区的这片城中村紧挨着三和人力市场,从南到北不过300步,在盖楼跟养蘑菇似的的深圳,它不起眼的程度跟不存在差不多,不过却是独一无二的地方——成千上万被称作“三和大神”的打工者,热爱这里自由堕落的生活,把它当作“心灵的港湾”。要论空虚,没有人比得过他们。

深圳三和地理位置示意图。
“你绝对可以,我好心跟你讲。”石头大哥劝我,这社会现实无情残酷,没一技傍身不行。他几年前在家乡欠下200万赌债,从福建一路嫖娼到新疆,又从新疆一路嫖回来,在三和多年,他从来没工作过,主业是赌博,副业是倒卖身份证银行卡,尤其擅长甜言蜜语,连服务他的小姐也乖乖地交出证件。不过,此时他正盘算着偷渡去缅甸。
“唉,现在三和不好玩了。”石头大哥叹口气,“以前这里都是车(站街女),‘哎老哥来玩啊’,还有义务的呢,‘走,姐赏你一炮。’”
“有这种好事?”
“红姐啊,你不知道吗?”他瞪圆了眼睛,仿佛不知道红姐是件了不得的事情。“得了艾滋病,死球了。”他说,可要是红姐还在,他也敢找,“人生不过一死,什么都要试一下”。
石头大哥收了手机,把背包从轮椅扶手挪到腿上,“连红姐都不知道。”他一边嘀咕,一边摇着座驾,消失在三联路的人流之中。
三和附近人来人往,行走其中,一个人正常的反应是觉得厌恶,各种叫人绝望的怪事都发生在这里:出租屋抬出一个人来,盖着白布送上救护车,啸叫着拉到不知道什么地方;打工者跟中介大打出手,疯了似的敲击人力市场的玻璃,动脉割破,鲜血洒了一地,起因只是工钱短了两块;一个自称“正宗三和大神”的家伙每逢挨饿,便四处找人打架,声称饿红了眼容易干坏事,只有痛痛快快打一架才能排遣。
就在城中村东面,一个人称“皮裤哥”的打工者,悄没声地饿晕过去,舒舒展展地摆成一个大字,下巴磕在水泥地上,骨头都快碎了。之所以十几天不吃饭,据他说是因为没有遇见慷慨解囊的好心人,旁人问为什么不去翻宝箱(垃圾箱),他恶狠狠瞪一眼,“关你什么事?”
连续上网打游戏不挪窝,有人坚持了三个月。由于三和有不打听姓名的潜规则,一律“屌毛”相称,所以只知道那“屌毛”从工厂出来,饥渴地钻进网吧,昼夜砍服,等到钱财耗尽、行李被网吧老板扔出门,他已经头发打结、浑身酸臭,走在大街上精神恍惚如大厦崩塌。为了在网吧多赖上一天,我见过不止一个人卖身份证、卖血、卖捡来的一片枕头,偷盗、抢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至于三和大神的数目,有人说几千,有人说两万,人群进进出出,即使有人想要统计也只会束手无策。但城中村80多栋六七层的民房,二层往上都住满人,10平米的房间摆着?6架双层铁床,公园、街角、网吧还有想象不到的角落也塞满了人。

三和街头聚集的“大神”们。
我想知道三和大神如何一步步落到这般田地,只不过,他们愿意跟你聊一切事情——坂田和沙尾哪里嫖娼更划算,怎么把一坨大便扔到主管脑袋上,特朗普的头发究竟是不是真的——但从来不愿意聊自己。我低价将身份证转卖给一个打工者,追在身后攀谈,他猛地转过身,作出凶狠的眼神,“你别跟着我!我不在现实里跟人说话。”
“你知不知道红姐?”我换了一种方式接近他们,打工者立刻变得兴致勃勃,“知道啊,死了。”“太老了,没搞头。”“别说知道,我还搞过,给了30块钱,你别说,心肠真挺好。”
据他们讲,三和大神的鼻祖、传说中的红姐现在很难见到,年轻的时候,红姐还叫阿红,后来年龄大了出来站街,她像侠女一样从人力市场走过,后面呼啦啦跟着几百人。红姐人好,不挑客,不少钟,真没见过这么仗义的人,不像老王,既是工头又是鸡头,带大神去打工,赚了钱回来再介绍个小姐一条龙榨干,只五分钟就赶你出来,太黑了。
早年三和附近有不少站街女,2014年警察围了老巷子,站街女跑光了,只剩下红姐。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太久没见过女性,眼睛都绿了,感觉红姐特别靓丽。可不知从哪天起,红姐也不见了。有人说,红姐赚够钱上了岸,嫁了好人家,还买了海景房,跟三和的垃圾们永别了。也有人像石头大哥那样,以为红姐得了艾滋,叫当年跟她好过的赶紧去查查。
后来历经周折,红姐终于在一家小旅馆里露了面,她穿着白衬衫、黑短裙,端庄地坐在椅子上,语气冷冷地问,“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
“我知道,我听他们讲过。”
“你直接说出来,没关系。”
我意识到她的用意,可也没空琢磨,“用我们的话讲,您可能是提供性服务的。”
她愣了一下,脸上的神情像瞅着一个呆子。之后的几天,她用远为粗俗的词语形容自己,又不断提起“尊严”这回事,前一秒还冷静自在,后一秒就红了眼、扯开嗓门,“我不要脸,因为我就是个最不要脸的人,我连饭都吃不上了,我要脸干什么?!”
猎物
按红姐的意思,她尚且保有尊严的时候并不算久远。四年前她在五星级酒店打零工,靠着婚宴上的红包攒了不少钱——有客人给的,有她偷偷拿的,两者界限也许不明显,她心理没负担。眼看攒够了五万,她却迷上了赌博,很快一无所有,恰巧又跟酒店起了冲突,工作就这么丢了。
可为什么要赌呢?哎呀,她说,不赌的话永远没机会。
眼看身无分文,红姐只能回到三和,她一出现,打工者立刻凑过来调笑,“红姐你日结(工资每日一结算)啊,是不是日完就结?”红姐豪放,不会拒绝他们的风流话,突然一个小伙子走上前,“姐姐我给你一百块钱。”红姐有些好奇,也有些荣幸,伸手接了。周围人开始起哄,把他俩像送入洞房一样推来搡去,没一会儿警察赶了过来。
想到可能要在派出所过一晚上,红姐哭了鼻子,警察指控她站街,红姐也没法反驳。离开派出所时,警察谴责小伙子,可越是咒骂,他越是寸步不离地跟着红姐。那晚之后,他们竟住到了一起。听小伙子说,哥哥开了电子厂、茶庄、酒楼,家里赚了几千万,但那指的是继父的家庭,他独自一人待在三和。红姐感到小伙把自己“像妈妈一样用”,甚至打算带她回家,说家里人怎么看他不在乎。一个月后,红姐逼走了这个23岁的年轻人,走时他哭得很伤心。
自那之后,站街这件不光彩的事她一直做了下来,“可能老天爷要让我吃这碗饭吧”。不过,命运的安排仿佛打开了一扇窗户,红姐透过男女之事这块半透明的玻璃,看到了三和大神们无能为力的灵魂,甚至也更加看清了自己。
从业后红姐常去网吧“找猎物”,一排人东倒西歪全睡着,跟“太平间尸体”没两样,大半夜精神了、快活了,杀啊砍的,要买装备要喝血,她站在那简直多余,打工者大多没那雅兴,有也是看看A片,抽空去厕所打个飞机,大神说了,“打飞机也只是想找个事做。”他们成月不出网吧门,经常迷迷糊糊打起来,冷不丁就动刀子,猝死的也不少,鼠标摁着摁着不动了,老板一摸才知道断了气,父母买了花圈跑来,天天吹喇叭,要毒网吧还儿子的命。也有打工者知道身体不行了,去城中村开个单间,过段时间躺平了被抬出来,红姐撞见的就有两回。
说起来有些残忍,但猝死只是三和最稀松平常、最无害的死亡方式。早几年,街巷里还有二三十个站街小妹,最小的只有16岁,“到了晚上,鬼哭狼嚎的”,红姐说,有一晚她住在旅馆里,听见铁棍声和一个男人撕心裂肺的喊叫,后来听说是欠了嫖资遭到毒打;一个站街女死在出租屋时,全身缠满一圈圈的胶带,身上有十几处刀口,行凶的也是一个欠了嫖资、被打坏了内脏的打工者;还有人在玩牌时,因为一点点输赢,突然抽出刀子,剁掉了对方的手掌。
如今情况大有改观,但红姐仍然小心翼翼地行事,做这行,“人家也算是给了点面子,你在眼皮底下做什么,别人心里清楚”。除了规矩,还有更多恼人的事情等着她应付。龙华公园里出没着两个酒鬼,醉时跟死尸似的躺着,醒时总来纠缠,“红姐,拿10块钱给我,我去买酒喝。”“红姐,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的**。”红姐不敢招惹,给了钱,好心相劝,“你不要这样喝,会没命的。”后来一个酒鬼被警察带走,另一个烂醉时摔了脑袋,拉到医院时已经断了气。
公园是打工者无处可去时最先想到的地方,但却是个不祥之地,除了酒鬼,红姐还在同一棵树下撞见过三个倒毙的大神。在公园睡觉时,如果身上还有财物,手机或者身份证,打工者就用塑料袋包好,在花园中挖个坑埋了,早上起来再挖出来。


红姐时常在公园遇见男同性恋者的聚会,大姐、二姐、三姐坐在一起织毛衣,老四看到红姐过来,热情地打招呼,“我美瞳你看还行吧?”他曾告诉红姐,以前饭都没得吃,自从做了男情妇,房子租了,金戒指也有了。红姐套过话,知道他并非真正的同性恋,但丧失了生存的能力,只能依附情人过日子。
大部分三和大神当然渴望接触女性,红姐知道这点,但平时遇见了,他们只顾着翻白眼,不敢像正常人一样有眼神接触。红姐每次在人力市场出现,大神们聚作一堆,掰开脑袋想看看一圈圈围着的究竟是谁,她简直“比范冰冰还范冰冰”。可当她主动跟大神说话,对方立刻就变了脸色。即便发生关系,红姐说,“大神更喜欢屁眼,不喜欢阴道,因为*了阴道女人骗他一辈子。”
我得承认,红姐讲述的事情超出了料想,在我的认知里,性之于人,既是最初的动机,也是最后的尊严,而三和大神的情状,已经不是简单的堕落与绝望,反而证明了红姐依据诸多事实得出的结论——那是“人格的毁灭”。
如今红姐极少在人力市场露面,但还时常接到大神的电话,与我聊天时,她的手机一次又一次响起,对方先是沉默,隔了很久才怯怯地问,“在哪里?”红姐挂断电话捋了捋头发,她有些不好意思,“可能你有人缘,平时就接一两个电话,今天突然这么多。”打来的电话有的找服务,有的只是聊天,说挣不到钱、娶不到老婆很苦恼,红姐就安慰他,“你只要努力,只要好好干,有钱了肯定能找到。”
红姐心肠好,愿意说些宽心话,可是,十多年来她自己也先后十次想要换个活法,去过武汉、厦门、陕北、鄂尔多斯、上海,受尽辛苦,最后一次回到三和后,再也不敢轻易离开。十年前她经常见到的大神,十年后还在这里。离开三和其实很容易,可要是落到精神瘫痪的地步,就得有长没短地挂着了。对此,红姐自己也深有体会。
女将军
如果时间一格格地倒转,龙华区的高档写字楼和成片的工厂会像积木一样悄然挪走,不出十年,便只剩下遍地芦苇和铁皮屋,回到“一片荒岛”般的景象,而天南海北鱼贯而来的打工仔也会比如今更加显眼——他们个个怀抱凉席、提着水桶,像蚂蚁一样聚在三和人力市场附近。红姐记得刚来三和时,局势更加混乱,明目张胆的抢劫者夺了她的财物,逗乐一样喊:“来追我呀!”红姐追不上,气得直掉眼泪,可她说,那会儿“每个人都充满了希望”。
28岁时,红姐被丈夫毒打一顿、扫地出门,从此开始了流浪生涯,小小的县城连洗碗的工作也没几个,她只能做了舞女,在歌厅录像厅一坐一整天。独自在外时,她总看见窗户上闪着白影,梦见小小的棺材装着7岁的儿子,但栖身之处不好找,“哪怕是糟老头,也要和他睡,为了一张床”。
红姐也有过好运气,结识了一个“男朋友”,兴冲冲地带回娘家,但大哥摔了碗,咒骂她,“离了婚你不要再回来!”在她的家乡,人生的体制远比想象的顽固和保守,在大哥眼里,如果不领了结婚的红本本,她带回去的就只是嫖客、下三滥。
伤心绝望的人,有时会将自己像颗石子似的扔出去,好碰碰运气。红姐离开家乡打工,磕磕绊绊,终于落到龙华区臭气熏天、墙角发霉的出租屋里,狭小的房间头挨头、脚挨脚住着十几个男女,但大伙儿你说我笑,路上遇见了,还会慢悠悠地问一句,阿红去哪里?红姐觉得安心,她甚至认了几个好姐妹,临别时抱头痛哭,约好常联系,只是后来没了踪影。
虽然三和混乱而凶险,但红姐不仅不害怕,“还把这里当做家”,她声称在三和找到了归属,“找到了活着的证据”。同样重要的理由还有,工厂里男工多,她觉得有盼头。然而,孤身一人、没有同乡照应,工厂对她并不友好,“主管的嘴巴跟孙悟空似的,屌得人眼泪下来”,红姐受够了气,冲着他大喊,“你这王八蛋,我不怕你!”后来换的工作多了,她疑心这根本就是一种管理风格,专找老的丑的手慢的,杀鸡儆猴给其他工人看,而她总是不幸中招。红姐不敢再进厂,一手创立了三和打零工的模式,最多时两个月竟赚了三千。
“感觉好刺激、好舒服。”她手舞足蹈地说,就像流浪一辈子的人突然有了大衣、突然当上了主席。有时日结也懒得干,一群人进厂“干跳楼”,关铡刀、拔电线,讨要精神损失费,红姐也跟着闹,她想一想,“以后还是个穷人,又不可能让我做一辈子,今天我也可以叉叉腰,也能出口气。”
在红姐风风火火像个女将军的2010年,龙华富士康连续发生了14起员工跳楼事件,据大神们说,自那之后,三和开始了它的“黄金时期”,聚集了越来越多只愿做日结的打工者。 三和轻松快活,“日结一天阔(可)以玩三天”,差不多成了一句暗号,在一众伤心又懒惰的打工者中间流传。
后来接受过红姐服务的人当中,我认识了打工者宋涛,也就是付了30块钱、觉得红姐心肠不错的那位。“那会儿没什么女人,全是男的,全是光杆司令。”当时宋涛看到红姐,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但事后又有些刻薄,认为红姐薄利多销,没什么智商,而且说实在的,太老了。
宋涛来到三和是在2011年,那时他惹了一身网瘾,揣着最后几块钱连夜赶来,下车时看到一排人躺在人力市场门口,个个扯个没完,说一时落魄,还告诉他“你不要怕,明早有日结”。早晨醒来,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堵得老巷子水泄不通,工头大喊一声,几十人跟着他,钻进大巴、送上工地和流水线,赚了钱再回到网吧接着瘫痪。宋涛惊呆了,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该来的地方。
和我走在城中村时,宋涛的表情很是凝重,好似望着被大火狠狠烧过的老房子,他指着一家网吧昏暗污浊的内部,“就那个地方,早上起来有个人不动了,没气了。”路过双丰面馆时,里面飘出一股多闻两下便要作呕的香味,老板娘从水桶捞出泡得发胀的猪肉,蹲在地上剁碎,头也不转扔进了锅里。胖厨师从来面无表情,不管你点什么,端上来的都是同一种黏糊糊的面条,4元一碗,十年来从未涨过价,宋涛说,他们管这叫“孟婆汤”。
网吧当中无法自拔的人各有各的理由。留守儿童小麦仰赖父母的歉疚,每月得到1000块的支援,只盼望成年的时刻晚一些到来,他表达“这样生活太爽了”靠的是一连串脏话,不堪入耳的程度连网吧老板也束手无策;在他身边,一个打工者一边盯着自己胸戴红花、光荣入伍的照片,一边唱着军歌,当他诉说完为了婚姻放弃军职却遭遇出轨的经历,抱着我的肩膀嚎啕大哭,“兄弟你不知道,我心里难受啊。当年的风流呢?哪里去了?”
宋涛的理由是无法忍受“那种眼神”。他自小父母离异,17岁出门打工后,羡慕别人举家在外、有所牵绊,而他孤独一人,四处碰壁。“走到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比较冷漠,人家根本不正眼瞧过你,但三和不存在这种眼神。”宋涛说,“大家不慌不忙、悠悠闲闲,好像没人歧视我,不存在什么‘高级的人’。”他用了跟红姐一样的词汇——“就好像找到归属感一样”。
宋涛曾以为,三和的快活日子能一直持续下去,但半年之后,他发觉心里的某样东西无声无息地垮掉了。
起初他们为了上网还愿意干活,时长日久,便像报废了的汽车,再也难以发动,“还有十几块钱,算了不做了,先上网,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很多人为省下网费,一天只吃一顿饭,能卖的东西也全卖了。实在没钱,便像个原始人一样在巷子里转来转去,希望碰见熟人,接济个五块十块。宋涛见过一位残疾人,一只手拍着键盘打“地下城”,大伙都羡慕他,催他赶紧去要饭,有天赋别浪费,可那家伙连要饭的勤快劲儿都没有。
后来聚集到三和的人越来越多,竞争更大,日结更少,一天早晨网吧散了场,“大家你问我,我问你,有日结吗?”宋涛看到,成百上千号打工者望来望去,几条巷子都堵满了。“都没日结,完蛋了。”
自从睡上了廉价床位,红姐也放松了脚步,姐妹们不再愿意去工作,只顾天南海北地聊天,或者干脆倒头大睡。“基本上一年四季在冬眠,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这样。”红姐想了想,“就是,也感觉到没意义。”
宋涛已经戒烟三个月,但这会儿又蹲在路边抽上了。一个打工者趿着拖鞋从我们身边一摇一摆地经过,他跟宋涛似乎认识,但谁也没说什么。三和不存在友谊这回事,6年来,宋涛甚至不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都是行尸走肉的,没人想知道别人的名字”。
我问他,难道不感到害怕?不想想40岁之后怎么办?
“你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想法,但三和大神是不正常的,明白吗?”宋涛语气急了:三和不允许你有那种想法,城中村都是要死不活的人,你只想随波逐流,一个星期之后都不愿去考虑,今天能过了就是好事。“人生没有什么盼头,一切为了游戏,忘掉外面的世界,忘掉一切的自卑,因为停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自己很悲哀。”
人的意志常常被误以为像开关一样,今天关上,明天还可以再打开,但像宋涛那样经历过一番才会明白,意志会锈蚀、腐化,当过了某个临界点,还会“叮”的一声骤然断裂,而更糟糕的事情往往还接踵而来。
孤魂野鬼
三和大神身无分文、无法劳动,想必毫无利用的价值。但周边发廊里的学徒不这么想,他们搬来半身镜,将打工者摁在座椅上,像剪羊毛似的练练手,两分钟后一拍肩膀,他们就顶着怪异的发型乐呵呵地走开了;城中村里的帮派更不会这么想,东北帮、河南帮、安徽帮、湖南帮,在大神挨饿时,递上5块饭钱,“养着”,不久就骗去做法定代表人、做分期贷款,如果有人质疑,难免被堵在角落里,拳脚相向。
宋涛也曾饿昏了头,交出身份证换来800元报酬,直到法院打了传票到家里才知道闯了祸。后来又兴起了“撸小贷”,我所见过最厉害的一个家伙,手机里整整三屏网贷APP,但他的态度是,凭本事借的,不还。这些都让三和大神越陷越深。
帮派横行的时候,红姐时常听到巷子传来凄惨的啼哭,“我的身份证被骗了!”跟她齐名的小黑是受骗之后才人尽皆知的,他勤快、爱干活,骗子骗走他的身份证,在网上发帖嘲笑他,小黑受不了,精神失常,从此走路不穿鞋,跟兔子一样连蹦带跳,还养了条流浪的小黄狗,有点相依为命的意思,后来小黄狗被人偷走吃了,小黑也消失不见。
打工者们结队上访,终于换来2014年三和的大清理。宋涛自此才醒悟过来,“因为活得太累了,真的很想死。”他进了南山的工厂,同去的三和大神干活有气无力,没过几天只想拿钱走人。不过,要是工厂有厂妹,他们“拼了老命也愿意多待几天”,宋涛说,虽然厂妹大多是穿金戴银的正式工,看不起邋邋遢遢的三和大神,但至少让他们觉得有盼头。只不过,近些年深圳的制造业少了,厂妹转去服务行业,很多工厂成了“和尚厂”,连这个念想也破灭了。
工期结束时,宋涛拿着5000块工资,茫然地站在工厂门口,“离开了这个厂,你又成了一个孤魂野鬼”。他仰着头不让眼泪掉下来,除了三和,他无处可去,又进入过去生活的循环。他说,三和的“那种共鸣太可怕了”。

城中村里网吧一家接着一家,转过路口,666网吧的老板正站在门前,逗弄着一只土狗,宋涛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在)这家网吧一口气待了7天”。其实后来他已经不能从游戏中得到任何愉悦,只有烦躁、自我厌恶,可还是走不掉。一切社会关系都已停止,他像在一片虚空里坠落,很想随手抓住点什么,好让自己停下,可这世界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给他预备。
六年来,他没有跟父亲说过话,“他不理解,你挣不到钱就是没用”。来三和前,宋涛有过一个女朋友,可随着那段关系不了了之,他彻底没了打算。即便成家有了后代,宋涛说,“他的人生很痛苦,干脆从我这点断了。”
红姐也发觉,很多三和大神已经断了组建家庭的念想,好几个人告诉她,“就算赚了几十万,也不娶老婆,因为一辈子的心血,不能交给一个女的。”但红姐自己不这么想,这点不同让她时不时还挣扎一两下。
如果找到一个人相依为命,红姐愿意跟他扫地、打零工,哪怕干到死也好。为了这事,她几乎到了心理扭曲的地步,在工厂干活,遇到合适的男工,红姐只想立刻黏住他,因为“等一下他回家,你再也见不到了”。
在三和十年,红姐认作老公的有三个,男朋友有三个,其中五个半都是三和大神,但每一个都让她伤了心。
遇见第一个老公的时候,他正在三和做小偷——勤于偷盗显示他对生活还有超出一般三和大神的热情,因此只能算半个——结识后两人回老家包了工地,一番辛苦攒了八万块钱。一天晚上,老公带着积蓄从侧门溜走,红姐坐上摩的,不停地催师傅快点。“不要命了,我车轮胎都要跑掉了。”慌乱间撞了车,红姐眼睛缝了13针。她不甘心,追到陕北,在一个光秃秃的、喝水要用骡子驮的山顶见到了老公的家,想找的人却不在那里。从陕北到鄂尔多斯,红姐带第二个老公回到三和,可他熬不住,带头闹事搅得工厂不得安宁。
一起生活两年后,红姐才发现第三个老公精神不正常,一开始还以为小伙子爱聊政治、很有才华,后来他一刻不停地说话,搞得三和大神们闻风丧胆,受不了的当场给他两耳光。原先在工地干活时,几千斤的吊篮砸下来,工友压成重伤,第三个老公压断了腿,打了八根钢钉,但从此震坏了脑袋,红姐寻思着有个伴也好,可他一天到晚不停地说话,红姐终于也忍受不了,单独租了个房子养着他,“现在我就当作是一条狗”。
头一个男友不愿住旅馆,宁愿独自到网吧睡,反反复复播放许嵩的几首情歌;第二个爱听《天空之城》《十里春风》,常常夜里十二点偷偷发短信。临近分手红姐才搞清楚,歌曲是他们前女友钟爱的,两人都放不下。红姐极力挽留,拉着袖子不让他们走,结果一个用酒瓶砸她,一个对她拳打脚踢。
白白遭了这些罪,红姐到头来还是孤单一人。“三个老公,(我)性欲也没有,爱情也没有,亲情也没了,感情也没了。”红姐说,两个男友相处一场,到头来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一聊起感情他们立刻封闭了自己。
有一段时间,红姐觉得可能自己的缘分不在三和,独自去了武汉、厦门、上海。上海消费高,跑到腿软也找不到便宜的旅馆;厦门海风大,红姐又冷又饿,在火车站睡了一晚。离开10次,又回来10次,她再也不敢折腾,身无分文却无需担心的地方,恐怕全世界只有三和,“大不了今天去发个传单嘛”。
跟我见面时,红姐刚刚和第三个男朋友分了手,她坐在椅子上挽起裤腿,晾出一块块淤青。“我连死的感觉都有,”她抬起头,“但女人真的很贱,他打得我这么惨,我还时时刻刻想念他。他打我,我拉他,他一直打,我一直拉,他走的那一天,整个龙华我疯了一样地找,很想很想找他过日子。”一年来,红姐维持着她所说的“这个家”,但男友对她只有敷衍,反倒与男性朋友亲近,等到发现了贴在网上的照片——男朋友穿着高跟鞋——红姐才明白,对方只是利用、玩弄自己。
尽管如此,红姐没法停下来,她依据自己心里的一点点渴望,认定三和大神只是缺少一份寄托,假如有一个父亲、一个兄长,或者一个爱人、朋友,事情会有所不同。“如果有个好家庭带他回家去,可能就重新开始了,如果没有,他们哪怕不在这里流浪,也会去别的地方。”
999朵玫瑰
台风引来的雨水在深圳落了三天,红姐再来时,带上了自己的徒弟林丽。
三和大神都知道林丽有些木讷,红姐解释说,小时候林丽的父亲犯了事,被枪毙,不知怎的,林丽记忆里竟然看到了那一幕,精神受了点刺激。两人第一次在龙华公园遇见时,林丽身无分文,照红姐说法,林丽刚开始“比较浪,见到男的就上”,认识她以后改了,至少知道收点钱。林丽想辩解,说当时也是为了有饭吃。
前不久红姐和林丽因为男人的事情闹了恩怨,红姐第三位男朋友走后,跟林丽凑到了一起,俩人吵了架,差点打起来。但没过多久,林丽也被抛弃。男人走了,她们反倒和好如初,继续做了姐妹。
这几年下来,林丽攒了几万块钱,红姐劝导她,既然有点饭钱了赶紧离开,别再让人骗了去,应该好好珍惜自己,再找个男人嫁了。林丽打算一个月后离开三和,红姐让她不要再来,否则,“我绝对会打你”。红姐自己赌了码,攒得少一些,但也说是最后一年在三和了,只是语气不那么确定。
早年还在家乡流浪时,红姐带过五六个小女孩,有几个是父母离异后抛弃的,相当于认红姐做了干妈,“不是做什么小姐,就是天天带着她们问人家要点吃的”。现如今,她们有的已经嫁了人。红姐说起这点小小的成就,脸上显得很自豪。
红姐打算离开的2017年夏天,三和又一次经历大清理,规定网吧不能通宵,民房不能群租,大神们开始迁徙,向着周边的弓村扩散,有的甚至打算集体迁往龙岗,但没过多久很多人又跑了回来。
我问红姐,你走了,三和几万大神,也许性需求还得要一个出口。
她同意,但觉得不该是她,她毕竟年龄大了,应该要个年轻一点的。红姐很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太多钱了,假如有,她想找个心理医生到三和,像教堂一样的,免费给大神们吃住。最主要的,她要招一些女孩,不是不健康那种,而是落魄的大神来了,拍拍他的肩膀、聊聊天,因为她自己无数次地想要得到那种安慰。“我有这种幻想。”她说。
只不过,红姐留在三和的传说太深入人心,不会有人关心她有什么幻想。
前两年有好事者将红姐的照片贴在了网上,她一下子成了名人,有人问她在三和怎么才能做鸭子,有人问她几号生日,要订制蛋糕送给她,也有的只是哇一声,感慨原来真的有红姐。据红姐说,年初的时候,上海的一个富二代订了丝袜、高跟鞋、999朵玫瑰送给她,打算带她像情侣一样去旅游。富二代来时开着路虎,也许是真人让他大失所望,勉强吃过西餐,他塞给红姐300块钱便离开了。
奇奇怪怪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好像全世界压抑苦闷的男人都知道了遥远的三和有自由快活的生活,知道了有位红姐,这让她有点不知所措。天津的一位高管慕名找来,许诺给她一整栋楼居住,还发来800元红包,问红姐是否能满足他激烈的性需求;北京某公司的小领导每次喝醉了酒就想起红姐,“老姐,你咋不来北京啊?”又说北京压力大,自己打打杀杀,好好的生意有人要跟他抢。
更多的人只是渴望过上自由自在、流浪般的生活,他们问红姐,三和怎么去?三和是否真如传言的那样迷人?
(本文采访完成于2017年夏天。文中宋涛、林丽、小麦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