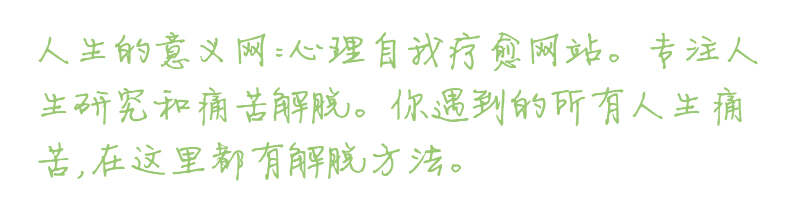王阳明心学批判:幼稚、低级的主观唯心主义
2019-01-08 08:23:40 发布:人生的意义网

王阳明心学批判:幼稚、低级的主观唯心主义
“心学”,就广义讲,指中国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论形态,就狭义讲,则指宋明时期的陆王心学流派。
这两种意义在王阳明哲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王阳明是中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哲学集中国心学之大成。他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论证世间一切事物都在人心内,依心而有,一切唯心,心外无物,从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直接提出宇宙与心知的关系问题,使其哲学带有中外主观唯心论的一般特点;他把具有封建道德观念特点的伦理本体引向内心,要人从内心深处去追求成为圣人、完人的真理,这又使他的哲学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乃至儒家哲学所特有的伦理型思维方式。因此,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武器剖析王阳明心学,找出它的本质特点,不仅可以使我们正确地总结理论思维教训,同样可以启迪我们的思想。以便加深对现代认识论所提出的,诸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主体在认识中所处的地位等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一、王阳明心学之“心”
王阳明心学之“心”包含了他以心为宇宙本体的基本思想,是其心学的基点和核心。为此,有必要先搞清“心”的含义。
王阳明哲学中本体之“心”的确立以“心即理”命题的提出为标志。他的“心即理”命题,针对朱熹“即物穷理”的“格物”方法所造成的“心、理为二之弊”,提出了在道德认识与修养过程中身心与事理相互统一的问题。他以为,朱熹把“心”与“理”(即主观与客观)分为两件事,“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答顾东桥书》,引自《王文成公全书》。以下只注篇名)也就是说,朱熹的认识论在主体方面以“心”作为“身”的主宰,而在客体方面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原,这样就分割了“身心”与“事理”,破坏了主体与客体在本体论方面的逻辑统一,其实还没有为客观性的精神本体找到最终的归宿。这在王阳明看来是不能容忍的。
王阳明主张“心即理”,一再申明“心、理是一个”,要人在心上“做功夫”,到心中去求“至善”的本体,这就把朱熹哲学本体论中能够生成万物的“理”本体,换成了与人的感官及认识直接联系的“心”本体和“知”本体,从而在道德修养和认识的范围内探讨世界的本质、“理”的来源问题。
王阳明对“心”的本质和内容有种种规定,但始终都没有离开“知”的范畴。
1.知觉之心与主宰之心。王阳明把“知”作为“心之本体”,认为“心”的本质是知觉,而这种知觉的灵明性也就是对全身动静的主宰作用。他说:
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传习录下》)
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传习录下》)
在认识主体方面,以心的能知作用和心对身的主宰关系来解释“心”,这是他的心学之“心”的基本含义,也是他与朱熹相同的方面。
2.把心、性等同并合为“良知”。与朱熹不同的,在于他把“性”也看做能知之性,从而在主体方面把心、性等同起来。他说:
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传习录上》)
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传习录上》)
但是,“性”的本来含义是指先验道德性。程朱“性即是理”的命题把封建道德性当作普遍的道德准则,并夸大为宇宙本体。王阳明沿袭了“性”的这种含义。就此来讲,他又认为“性”是“心之本体”,是“知”的真正源泉。他说:“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原不动,理原不动。”(《传习录上》)
“知”是心之本体,“性”亦是心之本体,可见“心之本体”是“知”“性”合一的产物。王阳明继承孟子的说法,把它叫做“良知”。他说:“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答陆原静书》),也就是把心所固有的知觉当作一种道德性知觉,以此来说明人的认识的来源。王阳明这样来概括他的心、性:
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答陆原静书》)
也就是说。他把先验的道德性.先天的认识能力及本能的心理情感合为一体,做为主体的知觉灵明,即“心”所固有的本质。
3.“良知”是“心、理合一之体”。王阳明既讲“性即理”,又讲“心即理”,他把心、性合一于“知”,这样就改变了“理”的性质,使之由客观的理变为主观的理(“心之理”)。他把程子的“在物为理”头上添一“心”字,为“此心在物则为理”(《传习录下》),表现了对“理”的性质的这种改变。他以为“知是理之灵处”,其主宰处叫做“心”,秉赋处叫做“性”,其实都只是一回事(见《传习录上》)。因此心能够自己认识自己,不必求之于外物。也就是说,“天理”本身具有“昭明灵觉”作用,这便是“良知”。“良知”既包括了“心之本体”(认识主体)的含义,又包括了“心之理”(认识客体)的含义,是一种圆满自足的认识本原,无所不该的宇宙本体。他说:“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凝,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传习录下》)他有时以“心、理合一之体”来说明这个特征,正表现了其心学之“心”将主、客体合一的本质特点。
王阳明对“心”的具体规定决定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基本特征。
首先,他以为认识来源于主体的心、性,从而把人对宇宙万物之理的认识归于心中固有的先验的道德观念、认识能力和道德情感,这就在认识来源方面割断了外物对心的源泉作用,腰截了以实践为基础的由物到心,由心到物的整个认识过程,而留下对由“心”到物的认识片断的发挥,其次,他的“良知”是一种主观性的、把主、客体合一的认识论本体,这就歪曲了认识的本质,由此决定他的哲学从认识的“能”、“所”方面论证心、物关系,以“能”消“所”,把客观外物消融于主观的心中,王阳明心学正是循着以上两个特点进行论证的。
二、王阳明论“心中之物”
王阳明对心、物关系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由心到物的认识过程中。他通过对“心—物”的认识环节中意念能动性的发挥和夸大,把作为认识对象的“物”融合在人的主观意念之中,从而取消了对象的客观存在。
王阳明的这一思想主要包含在他的“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和“知行合一”的命题之中。他从心、物关系中引伸出“心”,“意”、“知”和“事”、“行”、“物”几个方面的范畴,竭尽全力进行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消融工作。分析他的论证过程,其思维逻辑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对心、身关系的扩大
王阳明自称他的哲学为“身心之学”。事实上,其心学的全部奥秘也正在于对心、身关系的扩大。他把个体意识的心、身关系等同于认识活动的知、行关系,又由此而扩大到心、物关系,以此为基础,把客观存在的外物融合于主体道德践履的心、身活动之中。
心与身的关系,在王阳明看来,“心”处于支配的地位,“身”只不过是“心”的充塞处,主宰的对象,无心则无身,反之,无身则无心。他说:“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传习录下》)由此来看知与行,他以为所谓“知”、“行”,其实只是“心身之灵明”主宰与“身心之形体”运用的关系。他把知、行关系等同于心、身关系,强调了主体意识活动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但却排除了意识反映外界的客观内容,抹煞了实践对于认识的主导作用。但是王阳明并未就此止步,他进而把这种心身-一一知行关系扩大到心、物关系方面,以为心身心—知行一心物,没有什么不同,身、心、意、知、物都只是一件事。他说:“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功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传习录下》)他把作为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心、物关系等同于主体自身的心、身一一知、行关系,企图以此来窥见心、物关系的端倪。
2.从知、行关系中引出“意”的范畴,并把它运用到心、物关系之中。
“身、心、意、知、物”,其关键是个“意”字,“心之所发便是意”、“念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上》)他把“意”作为联系“心”、“物”的中间环节,而“意”的范畴是在知行关系中展开的。
“意”的最初来源是《大学》的“诚意”说。王阳明在解释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时,十分重视“诚意”,以为它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答顾东桥书》)。但他对“诚意”、“致知”、“格物”的解释却完全超出了《大学》的本意,而是就知、行意义上讲“意”、“知”、“物”的关系。他举道德修养活动为例,说明“意”即“意欲”,指打算做某事的意念,“知”是做好事情的具体知识,“物”是所要做的事情。“意”与“知”体现在“事”中,“诚意”、“致知”即在所要做的事中去实现符合“良知”的“意”,以达到知、行的统一。他把这个过程叫做“格物”。他的“格物”说,把“意”与“知”这些属于意识活动的现象放到“事”的范围内来说明,而“事”不仅包含受主观意向支配的道德践履活动,也包含客观存在的事物,他在此基础上突出强调“诚意”,也就是重视“意”对于知、行,以至心、物的联结作用。
王阳明把“诚意”之“意”进一步引伸、发挥为知、行关系中的意念之“意”,以此说明主观意念的能动作用。
意,即由“知”发“行”的主观意图。王阳明认为“知”与“行”合于“心之本体”“良知”,而体现“知”的“意”也是由心产生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知”决定“行”,它对“行”的支配作用,主要体现在心对意念的发动过程中,意念发动之时,也就是行为的开始。他说: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答顾东桥书》)
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传习录下》)
也就是说,“心”对“物”的作用表现在知、行关系中,一个人做什么事或不做什么事都首先决定于有没有此意念,一旦产生某种意念,就意味着即将开始某种行为,因此,“意”决定了事物的发生与进行的方向。心是发出意念的,而意念是决定行为方向的。这样,把“意”的能动性运用到心、物关系中,就得出“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的结论。
3.意、物的融合与颠倒
王阳明在知、行过程中夸大了意念的作用,又把心、物关系等同于知、行关系,于是就合乎逻辑地得出对“物,的概念的结论:“意所在之事谓之物。”(《大学问》)
“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把作为客体存在的认识对象——“物”主观化,当成了主观意向的产物,心的派生物。王阳明对“物”的意义的这一根本歪曲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
首先,他混同了“物”与“事”的概念。我国古代,“物”除指“天地万物”外,也包含有“事”的含义。但严格地讲,“事”与“物”并不能等同。“事”包括了事行,即实践的内容,而事行、实践虽是一种物质性活动,却又不同于自然过程的客观之“物”,而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朱熹讲“格物致知”,即训“物”为“事”,他说:“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大学章句》经一章)“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朱子语类》卷十五)“衣食动作,只是物”(同上,卷六十二),王阳明继承了“物”的这种含义。
其次,他颠倒了“意”与“物”的关系。“意”与“物”,就认识的本来规律讲,无疑是“物”在先,“意”在后,“意”源于“物”。因为人们的主观意图、念虑作为主体的动机、目的,虽然代表了实践中的主观因素,但就其最终源泉讲,还是源于对客观事物观律的认识,是“物”的反映。王阳明却颠倒了这一关系。他以为意念是由有先验之知的“心”发出的,来源于“心”的先验之知,而“物”是由“意”派生出来的,是“意之所用”。他说:
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答顾东桥书》)
意之所用,必有其物……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同上)
“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则明白宣布主观意念所指就是物,若没有意念就无所谓物的存在了。
王阳明就是这样,在由心到物的认识环节中,充分展开了“身”、“心”、“意”、“知”、“物”的范畴,论述了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其结果虽然颠倒了“心”与“物”的关系。
三、从“心中之物”到“天下之物”
以上讲的只是“心—物”关系中作为认识结果的“物”对于“心”的依赖关系。而王阳明要确立“心”作为万物本体在宇宙中的主宰地位,还不得不面对作为客观存在的“天下的关系。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把“天下之物”都当作“心”的认识对象,以此证明它们对于“心”的依赖关系。
王阳明认为,天下万物因受知于人而获得存在的意义,《传习录》中记载了他的有关“山中花树”的问答,说:
先生(王阳明)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下》)
山中花树,当人未去认识它时,它便与心“同归于寂”;而当人“来看此花时”,花与心发生联系,则此花颜色才在人心中“一时明白起来”。由此证明,花不在人心外。
王阳明又认为,“物”作为“心”的认识对象而存在,是因为“人心与物同体”,“心”与“物”有某种互相感应的能力。他说:“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传习录下》)“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同上)
这种“感应”能力的实质怎样呢?还须分析“感应之几”的命题。“感应之几”,就字义上说,“几者,动之微”(《易•系辞下》),这里指“事端”的意思。因此,所谓“感应”,可以理解为“心”与“物”在事端上的“感”与“应”,即“一念之发,一事之感”(《大学问》)的意念感应。这种感应产生在事物萌发之际,就“心”的方面,体现了发动意念的明觉作用,就“物”的方面,则体现了意念的活动与涉及。也就是说,在心为“知”,在物为“意”,“意之本体便是知”(《传习录上》),二者没有本质区别,都体现了心对物的“明觉感应”作用。所以他又说:“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答罗整庵少宰书》)
王阳明对心、物感应的描绘以及他对“意”与“知”性质的认识,从认识论方而来看,主要由于他对认识的两个不同阶段的颠倒与混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是基于实践的“物—心—物”的全部过程,其中既包括“物—心”,即思想反映外物的阶段,又包括“心—物”,即主观能动地作用于客观的过程。在这其中,“意”与“知”虽然同属于意识的范畴,但二者在主、客体的联系中处于不同的层次:“知”属于对外界客观事物的一种事实性认识,它直接与客体相关;而“意”是与主观联系更为密切的因素,这表现为人的主观意向直接地受主体认识能力的制约,同时在认识过程中对主体的活动方式及认识结果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和某些创造性作用。
王阳明由“感应之几”得出“心物同体”的结论,他认为“同体”的基础在于人心。因为人是天地万物之心,人心灵明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若没有这个灵明,也就没有天地万物了。他说:
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答季明德》)
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古凶灾样?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传习录下》)
至此,人的“灵明”,即主体的认识能力已经超越了认识的范围而成为“天地万物之主”,王阳明以“心”为宇宙主体的哲学世界观基本构成。他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下》)万物一体之相通处,在于“人心一点灵明”,这就是人的“良知”,也是天地万物的生意发端处。在《大学问》中,他把这种思想进一步阐发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他说: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
四、几点启示
列宁曾经讲过,唯心主义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朵。这告诉我们,彻底战胜一切唯心主义,并不单单是简单地驳斥一通了事,而应该认识到,认真地对他们作出深入的分析,深刻总结理论思维的教训,以至发现他们在某些方面对我们的启示,都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这正是我们研究唯心主义哲学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态度已给我们树立了典范。今天我们研究王阳明心学,也应如此。
上文分析表明,王阳明心学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它的理论体系的结构始终是围绕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路线来建立的。因此,认真剖析其认识论,从中吸取理论教益,无疑应该成为研究心学的重点。概括起来讲,主要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1.认识活动中主体客体的关系
王阳明心学以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为立论的方法和途径。他把本体论意义的心、物关系歪曲为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关系,以便从认识的能、所方面证明“物”对“心”的依赖。他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心”是“天地万物之主”,“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传习录上》),说明他已经将客体融于主体,用主观吞并了客观。这固然是荒谬的。但他在论述心、物的能、所关系时,同时又认为离心无物,离物亦无心,心、物相待而有,甚至说“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启发我们:认识本身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没有主、客体的相互作用。
王阳明心学的认识论是主张“内向”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他以为认识来源于主体的心性良知,是“心”所特有的天赋特性;他从主体的心、身关系出发探讨知、行及心、物问题,把认识歪曲为脱离社会实践的单纯意识活动;他把心身关系与心物关系等同,把认识的主体与客体集于人之一身,所以最终走上把主体当作本体,把“心”夸大为认识源泉和世界本原的主观唯心道路。同时,他的以主体为中心的认识路线对于我们认真研究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也是有所启迪的。现代认识论发展到今天,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主体自身在认识中的地位及作用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摆在人们面前,这就不仅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还需要结合现代自然科学知识,深人研究主体自身的各种因素,包括心理和生理等因素,正确估价它们对主体认识能力的影响以及对认识结果的制约作用。以往,我们的认识论可以说是“外向”型的,只单方面强调客体(环境)对主体的作用,忽视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因此,“内向”地探讨主体的作用,尤其显得重要。
2.认识活动的两个逆向过程
王阳明在描述人的认识过程时,以为万事万物以至于人类的“至善”之理是心中固有的,因此“心”首先通过对意念的发动,把本身固有之理分发给万事万物(由心到物的过程),然后万事万物才通过对心知的感应又回到心中(由物到心的过程)。他把人对客观的认识和反映变成了主体自身的内心体验,因此,作为主观意向的“意”与作为对客体认识的“知”,本质都是一样的,这就颠倒了两个不同的认识阶段,否定了客体是认识的源泉。然而在他对认识总体过程的歪曲反映中,也从某些方面以曲折的形式说明了认识的真实情形。这是因为:首先,辩证唯物主义把人的认识过程分析为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亦即由物到心,再由心到物的这样两个过程。
3.认识活动中的价值关系
中国古代哲学历来重视伦理道德。强调真与善的统一,把探求宇宙的真蒂与追求至善的真理结合在一起.故有“伦理型”哲学之称。王阳明也不例外,认识论与道德论相结合是他的心学的一大特征。王阳明把作为主体的“心”赋予先天伦理本性,从而把它列为作人和践履的准绳,固然有他力图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面,但同时我们也应从中看到共内在的合理性因素,这就是所谓人的认识活动中的价值关系问题。以往,我们对人与环境的关系往往只看到实践关系、认识关系,其实这是不全面的。马克思早就把人的需要、利益范畴引入主客体关系。他认为人们的任何实践活动本质上说都是实现某种价值成果的活动,活动对象就是人的利益的现实客体,主体同客体的这种利益关系而是价值关系。他还认为,追求某种价值目标不仅是实践活动的目的,也是理论认识的目的,价值关系是实践和认识活动的原动力。因此,人与环境的实践、认识关系中包含着价值体系,例如就认识的实践标准来讲:实践效果固然是判断人的认识正确与否的准绳,但对实践效果本身又存在一个评价问题。因此,价值关系应该成为认识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王阳明把封建伦理引入认识论,实际上也就是把人的利益需要纳入认识论。他的反动目的应当批判,但他在客观上把价值关系引入认识论,这是要进一步分析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