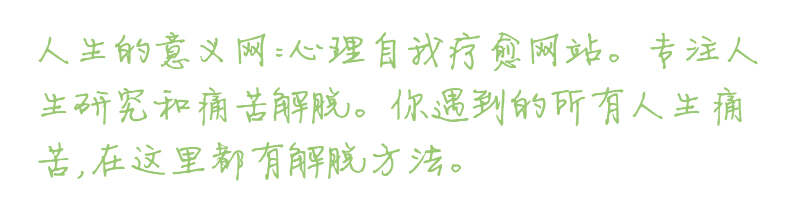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家关于生命意义的千年追寻
2016-10-09 16:34:31 发布:人生的意义网

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家关于生命意义的千年追寻
波斯大帝带着百万大军西征希腊,过海勒斯明海峡时,他站在将台上看他的大军由船桥上源源不断地渡过海峡,他忽然涕泗横流,向他的叔父说:“我想到人生的短促,看这样多的大军,百年之后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心里突然起了阵阵悲悯。”他的叔父回答说:“但是人生中还有更可哀的事哩。我们在世的时间虽然短促,世间没有一个人,无论在这大军之内或在这大军之外,能够那样的幸运,在一生中有好几次不原生而宁愿死。”
这个故事不由使人联想到生命的意义问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很短促的,至多不过百年而已,连波斯大帝也不由为此感到哀悯。然而正如其叔父所说,每个人在其一生中,却往往有好几次不愿生而宁愿死。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对生命的意义产生了偏差,他失却了前进的目标和方向,一时迷茫、困惑、不知所措,也就是所谓陷入了“生命的困境”。 何谓生命的意义?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苦苦思考着这个问题。生命,是一段历史,是一个过程。那么生命的意义,我想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时期,或者某一个固定不变的目标,而应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
一、 解读生命
何谓生命?根据自然科学的定义,生命是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在有养分的液体能够自行分化成两个完全一样的单位。这个过程是由一种我们成为DNA的物质控制的。然而,我们所要探寻的生命,却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而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生命,一种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生命。在这里,所谓的生命,一般意义上有两种:一种是整体意义上的生命,另一种则是指个体生命。由此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也随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整体意义上的生命,另一部分则研究个体意义上的生命,而且我们还要研究这两种不同意义生命之间的关系,这是不可或却的。
整体意义上的生命,我们亦可以称之为人类生命,是就人类种族的延续和人类历史的更新来说的。不管我们个体的生命如何,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各种族,不管是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抑或其他诸有色人种,都是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不断繁衍、不断进化的。尽管他们各自的历史命运往往是各各不同的。例如,非洲黑人在十五至十六世纪的二百年里,由于欧洲人的劫掠,被奴隶贩子贩往美洲谋取暴利。他们的命运是坎坷而悲惨的,每次贩运,都会有大半的黑人奴隶在航行途中由于饥渴或疫病而死亡。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里,非洲黑人青壮年劳动力损失近一亿,这也是非洲至今仍然贫困的原因之一。黑人为什么在美国一直受歧视,与他们祖先的这一段悲惨屈辱的历史是分不开的。而美洲的黄色人种印第安人的命运也同样多舛,在遭到从欧洲来的白种人的野蛮屠戮后,又从世代居住的土地上被赶往西部贫瘠的保留地。在迁徙途中,沿途留下了印第安人无尽的血与泪,为了铭记这一悲惨和屈辱的历史,印第安人称这一条路为“血泪之路”。正是由于这段悲惨的历史,本来土生土长的美洲印第安人,美洲的最初居住者和建设者,现在却沦为少数民族,他们的复兴之路又在哪里?真可谓“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可以说,在从十六、七世界开始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无疑是欧洲和美洲的白种人完全占据了世界的主导地位。先是欧洲人,如荷兰、西班牙、英法的相继称霸天下,然后是美洲人主要是美国人在十九世纪末的强势崛起,并且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蠢蠢欲动”和“二战”的力量蓄积,最终攫取了世界霸权,并开始了其独霸世界的历史。然而,人们只是看到了胜利者的得意的骄傲的大笑,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去注意那些在战争中无辜罹难的千千万万的生灵呢?德国法西斯,1939年,波兰,“排犹运动”,六百多万犹太人遭疯狂杀戮,有名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将这血腥的一刻永远镌刻在人类灾难历史的十字架上。为此,德国人一直在忏悔,道歉,而西方的基督教神学家都宣称,基督教的教义教规必须正视人类这一悲剧,并有针对性地做出态度的改变和调整。天主教神学家默茨提出:绝不存在一种能漠视奥斯维辛去拯救的历史意义,绝不存在一种能漠视奥斯维辛去维护的历史真理,也绝不存在一位能漠视奥斯维辛去祈告的历史之上帝。基督神学必须能够在历史的否定性中去感受历史,即在历史的灾难性本质中去感受历史。从实践——政治的角度记住每一位受难者,应成为基督神学的内在要求。”
然而,日本人呢,且不说在亚洲其他国家犯下的滔天罪行,仅就中国来说,南京大屠杀,三十余万生灵悉遭涂炭,而日本人竟然拒绝承认历史,甚至在其历史教科书上对其侵华战争进行美化和粉饰。同样的历史,同样的悲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对此的态度竟有如此之反差,的确不能不令人为之忧思。
人类的整体生命其实就是在这数不清的灾难,如瘟疫、战争、饥荒、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的洗礼下不断成长和延续的。在经过数不清的与瘟疫和自然灾害斗争之后,在经历了各种漫长或短暂的历史战争之后,人类又开始了生命的新的跋涉。战争的残酷性是不消说的,仅仅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有逾亿人死于战乱和炮火,而上世纪末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本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在高科技卫星制导武器的精准打击下,又不知有多少的官兵和平民死于非命。
各种各样的瘟疫和疾病,无疑是威胁人类生命的又一大疾患。象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曾使欧洲人口损失近一半。天花与麻疹也是曾经让人谈之色变的疾病,直至研制出了专门预防其的疫苗;而在当今社会,尽管医学高度发达,可是仍然有一些疾病还未找到预防和根治的有效方法,比如“世纪瘟疫”AIDS,还有世纪初在中国部分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广泛传播且死亡率很高的SARS。虽然不及AIDS一样一旦患上便极少有幸存者,但其患病的几率、传播的速度、蔓延和扩散的时间都比AIDS还要高,还要快。
而数不清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火山喷发,泥石流,旱灾,水灾,等等,无疑是长期笼罩在人类心头的挥之不去的阴影。火山喷发,泥石流,旱灾,水灾,且先不必说了,单是地震和海啸已经成了世纪初人类生命灾难和悲剧的代名词。世界各地接连几起大地震,土耳其,印度,中国,以及刚刚过去不久的东南亚海啸,成千上万的无辜生命顷刻间戛然而止,怎不令人震惊和痛惜?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两个世纪的确是人类多灾多难的世纪。而在这一系列灾难发生期间,那些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是否能够重新唤起我们已经久违的善良温暖的人性?我们在期待着。
个体意义上的生命,是指作为整体意义生命的一分子、一部分、一个微小的颗粒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是微末的,是异常渺小和脆弱的,就好比“沧海一粟”,就如同一位作家形容的那样“甚至经不起头顶落下的一块小小的瓦片”。个体生命必须在整体生命中才能获得他生存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如食物、住房、爱与关怀、社会尊重、个人成就感等,否则他便会“孤独地死去”。也许你会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那个人不照样生活的好好的吗?而且还非常令人神往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鲁滨逊是在一种不情愿的情况下才会在那个海中孤岛上定居下来的,他是为了生存才去学会逐步适应荒无人烟的孤独生活,学会去种植作物、蔬菜,捕猎,仿佛又回到了原始社会。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他也开始变得麻木呆滞,甚至已经失去了时间观念。这在常人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啊。而故事的结尾,鲁滨逊最终被人解救,回到他原先居住的村落。从他本心来说,在他荒岛孤居生活的日子里,他是非常渴望回到人类社会生活中去的。尽管这一观念随着一天天的等待和失望而变得日益模糊。而某些小说评论家在评论这部小说时,称其为早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化身,表现了一种向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的欲望,就其本身来说,又是多么的不合事实与逻辑。
个体生命固然离不开整体生命,整体生命也是同样离不开个体生命而独立存在的。这就是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整体与个体、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没有一个个个体生命的存在,人们会有“人类”这一概念的产生吗?绝不会有。那样的话,也就不会有保尔所说的那一句“为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话存在了。
在我国古代诸子百家的作品中,有关这方面的描述也屡见不鲜,例如“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涓流,无以成江海”,另外再比如“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等,都无不说明了整体对于个体的一种依赖性。
要之,个体生命离不开整体生命,离开了整体生命,它便失去了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整体生命也离不开个体生命,离开了个体生命,它便失去了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
二、 生命的意义
何谓生命的意义?也就是生命存在的目的,通俗地说就是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并不简单的哲学命题。他不仅反映了一个人的价值趋向,也放映了一个人为人处事的基本立足点,说到底它是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从古希腊到中世纪,一直到近代和现代,历史上数不清的哲学家对于这一问题做出了他们各个不尽相同的回答,我们可以沿着他们的足迹,一路追寻下去。
(一)德谟克利特的幸福主义生命观
德谟克利特是古希腊最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创立的原子论唯物主义哲学是早期自然哲学的最高成果,是古代哲学繁荣的标志之一。他创立了幸福主义的生命观,他主张构成理性的原子是圆滑和精致的,构成感性的原子是暗淡而粗糙的,两种原子构成了两种认识,也形成了两种幸福和快乐,即肉体的快乐及心灵的幸福和快乐。
德谟克利特认为必要的物质享乐是合理的。他说:“一生没有宴饮就象一条长路没有旅店一样。”[1]他还说:“应该深切体会到人生是变幻无常。它常为许多不幸和困难所烦扰,因此应该仅仅只要安排一个中等的财富,并且把巨大的努力限制在严格的必须的东西上。”[2]但是,德谟克利特又认为,幸福和快乐不是纯粹的感性享乐和物质刺激,无约束的物质欲望是暗淡而粗糙的原子刺激的结果,虽然有时是必需的,但往往又是带来与人的幸福的愿望相反的后果。为避免这种后果,首先要节制欲望。他说:
节制使快乐增加并使享受更加强烈。[3]
应当拒绝一切无益的享乐。[4]
其次,要做到心灵的安适和宁静。他认为:生活的目的是灵魂的安宁。这和某些人由于误解而与它混同起来的快乐并不是一回事。由于这种安宁,灵魂平静安泰地生活着,不为任何恐惧迷信或其他情感所扰。[5]
德谟克利特认为,心灵的享受是圆滑和精致原子的作用的结果,是真正的幸福和快乐;而一味追求物质享受,则是虚假的幸福和快乐。前者是崇高和永久的,后者是低级和短暂的。人生的目的和准则,就是求得精神的幸福和节制物欲。德谟克利特的快乐和幸福的观点,既不同于唯神论的观点,即精神就是一切的观点,也不同于庸俗的享乐主义,而是一种合理的幸福主义,在节制基础上的快乐主义。
德谟克利特利用两种颜色、性质不同的原子来指代感性与理性、肉体与心灵,是很富有想象力的。他认为必要的物质享乐是合理的,也是非常正确的。他认为幸福和快乐不是纯粹的感性享乐和物质刺激,虽然有时是必需的,但往往又是带来与人的幸福的愿望相反的后果。为避免这种后果,首先要节制欲望。这一点与后面提到的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生命观是极为相似的,他正确地指出了人们应该节制欲望,特别是那些并不是人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欲望,否则便会反生痛苦。而他认为,心灵的享受是真正的幸福和快乐;而一味追求物质享受,则是虚假的幸福和快乐。前者是崇高和永久的,后者是低级和短暂的。人生的目的和准则,就是求得精神的幸福和节制物欲。这些观点都是独到而深刻的,它凸显了人之为人的一面,即精神的快乐是真正的、持久的、高尚的快乐,而单纯地一味地追求物欲则是虚假的、短暂的、低级的快乐。在追求必要的物质财富以及合理性方面,德谟克利特的思想与儒家的“中庸”思想不谋而合,孔子曾说过“过犹不及”,而《中庸》中亦明确提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儒家是非常注重人的道德和行为的合理性的,南宋朱熹更是将儒家这一思想推向极致,提出了“天理”的学说,从而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局面。
(二)犬儒学派与昔勒尼学派的对立的生命观
犬儒学派的重要代表第偶根尼,主张人生要过简单纯朴的生活,回到所谓的自然状态中去,独立自主地活着,幻想离开现实社会过安贫乐道的生活。犬儒学派的机遇主义思想反映了希腊城邦奴隶占有制已经逐步走向衰落,他们的思想是消极的。我想犬儒学派的这一思想颇类似于中国的老庄那一套思想,他们是主张出世或避世的,而不像儒家那样主要主张积极入世,因为儒家也不乏出世或避世思想,例如孔子在《论语》中所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
与犬儒学派同一时期的希勒尼学派却与之持截然相反的看法。这个学派的基本哲学主张是感觉主义。其创始人昔勒尼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寻找快乐,故被称为“唯思乐派”。其所说得快了包括肉体快乐和精神快乐。但他们认为,重要的快乐是身体的快乐和直接的当下的快乐。快乐不是无节制的,人们应当成为快乐的主宰而不能让快乐主宰人,不然反得痛苦。用感觉主义说明快乐主义,是这个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
“唯思乐派”的这一主张似乎与当下很多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亦非常注重快乐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将追求快乐作为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找乐子去”,就是极形象的体现和说明。不过现代人所追求的快乐,虽然两方面的快乐都包括,但似乎更倾向于肉体的快乐,像吸毒和嫖娼的增长即是其表征。现代人精神空虚啊,所以他就拼命追求肉体的快乐,追求那种片刻的和当下的满足,而吸毒和嫖娼恰恰迎合了他们的这种心理。紧随而至,像“艾滋小偷”、性病的传播蔓延等诸种社会弊病就出现了。在这里,我觉得现代人应该多学习一下“唯思乐派”的做法。人,毕竟是理性的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注意有所节制。快乐不是无节制的,所谓乐极生悲,人们应当成为快乐的主宰而不能让快乐主宰人,不然反得痛苦。现代人的痛苦也恰恰由于不能对快乐有所节制。
(三)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生命观
与昔勒尼派遥相互应的是晚期希腊的哲学家伊壁鸠鲁,他提倡快乐主义的生命观。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在谈到快乐时他说:
我们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6]
伊壁鸠鲁所说的快乐、幸福首先是以一定的物质欲望的满足为条件的;但是在他看来,寻求快乐并不要求满足一切欲望,只是要求满足保持生命和健康的必要的欲望。
伊还认为,除物质的快乐外,还应有精神的快乐,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更大的快乐。可见,伊的快乐主义,又不同于无休止追求感觉享受的纵欲主义,而是要求保持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宁静。这种快乐是最高的理想生活境界,也是道德的表现。他说:
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宁静,乃是幸福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才竭力以求避免痛苦和恐惧。我们一旦达到了这种境地,灵魂的骚动就消散了[7]
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观是非常深刻的。人之生存,必须以具有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前提,否则生命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其必要的基础和前提。但是,人的欲望是无有止境的,所谓欲壑难填,要得到快乐,是否就必须满足其所有的欲望呢?当然不可能。所以伊氏才说,只是要求满足保持生命和健康的必要的欲望。这与“唯思乐派”一样,都是强调对于快乐要有所节制,否则不仅反生痛苦,而且生命和健康也必然遭受其害。此外,伊氏非常注重精神的快乐,并指出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更大的快乐,这一点也是非常深刻的。人之为人,恰恰在于他有精神,有意识,有思想,而这是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所以,他就需要比其他动物应有更高的目标和追求,而这就体现在他更为重视精神的快乐和满足。否则,只追求肉体的享乐和满足,那和其他动物又有什么两样?人们管这种人的理想叫做“猪栏理想”。
(四)十五、十六世纪人文主义者的生命观
十五、十六世纪被称作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此时哲学的研究对象从面向神转变为面向人和自然。在批判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斗争中,以人和自然为中心的人文主义、自然哲学思潮蓬勃兴起,开辟了欧洲哲学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是抬高人的地位,贬抑神的地位。他们称颂人的价值尊严,反对对人的蔑视;赞美人的世俗生活,反对禁欲主义;重视理性和知识,反对盲目信仰;提倡个性解放,桎梏和封建等级制度。[8]
享受现实的幸福,追求肉体的快乐,满足尘世的生活,是人文主义者所了解的人的本性的重要内容。佩脱克大声疾呼:
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足够了。这是我所追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9]
此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所谓性爱。薄伽丘说:
在所存的自然的力量中,爱情的力量是不受约束和阻拦的。[10]
神学认为,要求实现人的肉体幸福,这是短暂的,虚假的,是恶行和愚昧的表现;人文主义者则认为人的生存和意义就在于这种本性的满足,这是完全适当的,而且是世界存在的前提。可以说,人文主义者的激进的思想,是对中世纪神学禁欲主义的一种“大反动”。其产生的影响和结果是非常深远和广泛的,并且成为西方传统文化及精神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诚如刘晓枫先生所言,文艺复兴在历经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之后,本世纪是否将继续东移,来到我们中国呢?这的确是一个颇令人兴奋和值得期待的课题。那么,且作一乐观假设,文艺复兴诚降临到中国,那么我们必须做好哪些准备好什么,来迎接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呢?十五、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和范例。我们应该积极地汲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在文化精神建设方面,更需要我们去参照和学习。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像儒家、道家和佛家文化?我们应该如何迎接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挑战和冲击?我们是否需要继续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灿烂精神之花?这一个个课题都是很值得现代人思考和回答的。
(五)叔本华的“摩耶之幕”
叔本华是十九世纪一位著名的悲观主义哲学家。他对人生持消极的否定态度,认为人生不值得人们去生活。他认为,人生没有意义,人生就是痛苦。只要人活着,痛苦就不能解脱。既然人生是痛苦的,没有意义可言,那么就不值得人们去生活。他说,人想为快活而生存,其实这是一个生来的错误。世界是怀疑、错误、罪恶、疯狂的领土,人生大部分是梦幻,是通往死亡的路程。历史就是人类一个长期艰难的梦。一切都是相对的、暂时的,只有欲望是永恒的。从根本上说,人是不应该存在的东西。所以人不能不死,死是生存欲望在经过痛苦历程之后对错误的改正,也是对人们生存错误的一种惩罚。所谓追求幸福,只不过是被“摩耶之幕”遮住了眼睛。
叔本华断然宣示:生命,整个地根本就是痛苦,每一部生命史都是痛苦史,人生就是苦难,世界就是地狱。
叔本华最后指出,要得到永久的解放,就要彻底否定生命意志。最好的途径是象基督教禁欲主义者和佛教徒所践行的那样,在禁欲的生活中完全放弃意志以达到遁世绝欲,超脱痛苦。具体办法分为三个步骤:自愿放弃性欲;甘于痛苦;死亡寂灭。[11]
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和悲观主义迎合了德国资产阶级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悲观、懊恼情绪,为意志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则是它的进一步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曾经在中国的大学校园乃至社会上广为流行,深受很大一批人的欢迎,甚至被奉若圭臬,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是很符合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心理的。那个时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十年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刚刚从文革的梦魇中觉醒过来,寻找新的精神出路而未得的时候。文革的结束,宣布了一代人理想主义的彻底破灭,国家将往何处去?社会将往何处去?人生该往何处去?一系列的迷茫和困惑交织,人们犹豫,彷徨,苦闷,孤独,而此时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不失时机地来到中国,人们仿佛在黑夜中找到了引向光明的星火,他们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原来在西方他们还有一个如此难得的知音哪。由是,我们便又明白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因为该哲学恰恰反映了那一时代人们的普遍心理和精神需求,并未他们带来一些解救的途径和良方。
(六)海德格尔的生命观
海德格尔是20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创立了存在主义的哲学系统,并且是德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
海氏认为“此在”在世的基本状态是烦、畏、死。首先,海氏认为,“此在”在世就必然与他人他物共在,与他人他物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个过程的基本状态就是烦。他把“此在”与他物之间的关系称为“烦心”;“此在”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称为“麻烦”。在现实社会中,人越具有社会性,就越失去个性,失去自由,感到烦恼,从而产生麻烦这种内心情感。
其次,畏惧。海氏指出,畏惧和日常生活中的害怕是不同的。日常生活中所害怕的对象是看得见,摸得着,说得出的,但人对他所畏惧的东西却说不出所以然来,它至大无边,无所不包。:正如其所说“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12]
最后,死亡。海氏强调,死亡对人的存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此在”在世必须对自我、对自己的存在有真正体验。只有死亡,才是人生的终结,是“此在”本质的完全体现。海氏指出,死是最独特的、最不连贯的、最不可替代的。
海氏的死亡观是独特而富有深刻的人生哲理的。它预示着个体的独立和苏醒,但是却又是厌世和消极的,正如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生存意志哲学一样。海氏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人越具有社会性,就越失去个性,失去自由,感到烦恼,从而产生麻烦这种内心情感。这一观点很受诸多学者的认同,特别像现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读刘晓枫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于此点感觉尤为迫切。他写流亡话语,写意识形态,写知识分子的信仰,无不体现出这么一层思想: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由于各种主义的影响,人们的思想只能被社会或集体等“空虚”的概念所束缚,而自己的个体性却得不到尊重和发挥。于是,便有了追求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流亡,于是就有了流亡话语的产生。这种流亡,不仅有外在的流亡,还有内在的流亡(即身在国内而仍坚持思想独立和追求个性的知识分子),相对来说,内在的流亡比外在的流亡会更痛苦。二战期间,由于希特勒的高压政策,德国大批知识分子包括一些科学家流亡美国,从而产生了德国的流亡文学和文化;1922年和1924年,苏俄将一大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使他们在欧洲如德国,法国,英国等流亡。于是,便产生了苏俄的独特的流亡文学。
刘晓枫也对“畏”(他用的是“怕”)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和概括,并将海氏的“畏”包括进自己的第二种理解中,即面临虚无的畏惧心理。另外,他还提出了对“畏”的第三种理解:我所说的那种怕与任何形式的畏惧和懦怯都不相干,而是与羞涩和虔敬相关。这种怕将那永恒神圣的天父藏匿于自身,所以不是面临虚无之畏惧。只不过,从对虚无的畏惧可能感受到圣经中所昭示的这种怕。因为,当人面临虚无时,也许会翻然悔悟其自身的渺小和欠缺,进而承纳神灵于自身。以羞涩和虔敬为质素的怕,乃是生命之灵魂进入荣耀圣神的虔信的意向体验形式。(《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重温《金蔷薇》》看来,他的这种“畏”乃是一种宗教体验与感悟,与平常我们所理解的“畏”有着很大的不同。
三、生命意义的追寻
在对历史上不同时期哲学家针对生命意义所作的回答进行了一番赘述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有关生命意义的回答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快乐主义或者说幸福主义的生命观和禁欲主义或悲观主义的生命观。通过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以德谟克利特、昔勒尼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十五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者等为代表,他们的生命观属于快乐主义或幸福主义的生命观;而犬儒学派、中世纪神学、叔本华及海德格尔为代表,他们的生命观则属于禁欲主义的生命观。
快乐主义或幸福主义的生命观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追求生命的快乐和幸福,充分享受生命和生活的乐趣。这种快乐和幸福主要包括两部分,即物质的快乐和幸福(如财富的积累与感官的需要与满足)和精神或心灵方面的快乐幸福(主要指心灵的宁静与灵魂的安宁)。而他们的所谓快乐或幸福,还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现实性。也就是说,他们追逐的快乐幸福是在现实世界中通过个人努力能够最终实现的,而非寄托于神、上帝或者来世。他们非常重视心灵或精神的快乐,也就是心灵或精神的安宁与闲适,有的甚至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快乐。他们这种生命观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和无神论思想。
反之,禁欲主义或悲观主义的生命哲学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感叹与生命的短暂与世事的无常,对现实充满了犹豫、迷茫与困惑,将希望寄托于神、上帝或者期望借压抑本能欲望乃至通过死亡以达到生活的安宁和灵魂的安静。相犬儒学派的所谓安贫乐道、无欲无求的自然生活;叔本华的生命的本质是痛苦和希望在禁欲的生活中完全放弃意志以达到通过绝欲超脱痛苦以及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世的基本状态是烦、畏、死,只有死亡才是人生的终结,是“此在”本质的完全体现,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哲学派别的哲学家,他们的对生命意义的看法往往是不尽相同乃至截然相反的。比如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大多倾向于快乐主义或幸福注意,例如德谟克利特、昔勒尼学派及伊壁鸠鲁学派。而在漫长的中世纪里,禁欲主义或悲观主义则无疑如同一张巨大的黑色天幕将一切光明笼罩,人们的生活以及心灵都被宗教禁欲主义的枷锁牢牢套住。而在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人的意识的逐渐觉醒,打破神学和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追求现世的快乐和幸福成为一股不可遏抑的历史潮流;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者则把生命看作一台机器,将生命的意义束缚在极为狭小的范围,用自然的机械、静止、孤立的眼光来看待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自从进入到现代社会,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兴起,世界上的物质财富也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增加,人们更多地将眼光放在财富的积累以及现实的物质享乐,而却忽视了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与探索。也许这也就是所谓的人的异化吧。
现代的人,正在逐渐失去所谓的万物灵长的地位,而逐渐沦为物质和金钱的奴隶,他们失去的东西,并不是以多少的金钱和财富能够衡量的。人,之所以能异于动物,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能思维,“人类的思维是世界上最美的花朵”(恩格斯)。而这种思维的最高实现就是人类能够赋予万事万物以意义。正是在它的指引下,人类才能不断深化着对世界的认识并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先进工具,不断地改造着周围的世界,形成人化的自然。而当这一世界上最美的花朵日趋于枯萎和凋零的时候,那么他们正逐步将自己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他们失去了前进的目标、动力和方向。
追寻生命的意义,是千百年来所有有感于生命的短暂以及人生的坎坷曲折的人所孜孜不倦加以求索的永恒课题。而愈是靠近现代,这种探索和追寻却反倒越来越少,几至绝迹,这是历史和生命所不能容许的。找寻到了生命的意义,历史的车轮才会沿着正确的方向滚滚向前;找寻到了生命的意义,个体的生命才会在岁月的轮回中向着人生终极的目标坚定地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