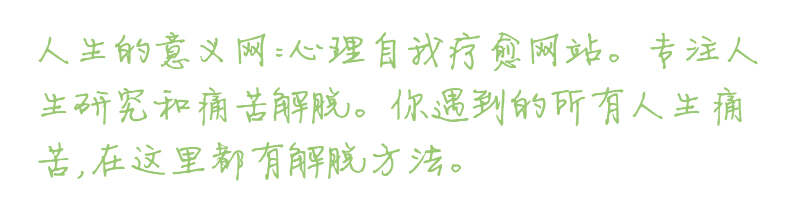空心病|人活着是没有意义的
2017-01-04 10:53:22 发布:人生的意义网

空心病|人活着是没有意义的
人活着是没有意义的。前段时间,四成北大新生患“空心病”的新闻,引起大家热烈讨论。所谓“空心病”,是北大徐凯文老师提出的概念。它的典型症状是不知道“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活着”。
大家对“空心病”的讨论,逐渐分化为两种声音,两种“派别”。一种认为,“空心病”是受到应试教育体制荼毒的结果,学生只知道念死书,考高分,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所谓“空心病”,其实正指出了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甚至是人们不敢面对的真相:人生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
今天我们无意从学理上去争论谁对谁错。只是很坦诚地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意义”困境中挣扎的人的所思所想。分享这样的过程,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可能在于:让有同样挣扎的人知道,你并不是一个人;并且,你可以试图与这种挣扎共存。
这是一个人寻找“意义”,最终与“无意义感”共存的故事。你一定也经历过这样的寻找,那么你的故事是什么?如果你愿意,欢迎留言给书评君,与大家分享你的寻找与挣扎。
1
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而是活力
从小到大,我大概都算不上是一个“快乐”的人。我甚至怀疑,“快乐”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过总体而言,也有喜有乐,有愁有忧地过来了,没有什么不同。
但最近的一两年,“不快乐”的状态开始从意识层面转移到了现实生活里:我逐渐无法维持正常的工作、生活运转。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成为负担。早上醒来,没有任何动力起床,想到又要开始新的一天,心里没有任何期待,充斥的全是麻木及不耐烦。不耐烦什么呢?所有的一切。比如要坐起来,要穿衣服,要洗漱,要吃饭,要回微信,要接电话,要开会,要跟人聊天打趣,要…活着。
对,大概就是对“活着”这件事情,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失去了耐心。连吃饭也成为负担。我的工作需要大量写作,但我对着电脑屏幕一整天却敲不出一个字。对人际交往的欲望似乎也已经消失,我近一两年从来不会主动联系朋友,从来不会主动跟朋友约吃饭、逛街或聊天。如果可以,我最大的欲望只剩下躺在床上保持静止。
我对此的处理方法,是忍耐、压制及强制的鼓励。面对自己,是忍耐和压制:觉察到心里那些排山倒海般无能为力的绝望感,然后摁住它们,压下它们,忍耐它们。面对外界,则强行给自己打鸡血,尽力维持过得去的状态:写不出来,熬夜硬写;不想出门,揪着自己的头皮硬出;不想说话不想交际,但会使尽全身力气在脸上挤出一个微笑。
后来的某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突然在聊天的间隙说了句:“我觉得你有抑郁症。你要不去查查吧。”美国著名作家安德鲁·所罗门在TED所做的关于抑郁症的演讲流传甚广,他在其中说道:“抑郁的反面,并非快乐,而是活力。”这个说法一语中的。
如果照此推论,我可能的确是抑郁症?生命的活力被抽空了。但是我同时对一切命名,保持着强烈的怀疑。不用说远古时代,就是在二三十年前,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抑郁症”这个词儿。我们的父辈,他们那一代人难道没有心情低落、辗转反侧、生无可恋的感觉吗?他们当中有人患抑郁症吗?他们是如何处理的?对生活的不耐烦、不投入就是抑郁症吗?还是时下更流行的,“空心病”?
到了今年夏天,由于在个人感情上也遇到了变故,我感觉自己的心理防线终于全线崩塌了:那最后一点伪装的力气,也消失了。我只能承认:自己的状态的确出了问题。想了一圈儿,我没有去医院检查,选择了去做心理咨询。
2
人人都有求生欲,人人也都有求死欲
去做心理咨询之前,我将它看作是自己的救命稻草。
心理咨询师问我: 你对我们的咨询有什么期待?我说: 我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对一切失去兴趣?并且,我希望能够通过咨询,让自己的状态好起来,积极地面对生活和工作。心理咨询师笑而不语。他是一个很温和包容的人,不管我说什么,他永远都报以最专注的聆听和接纳。咨询中,他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的感受是什么?#p#分页标题#e#
咨询持续了整个夏天,我不能说它是毫无作用的。它令我离自己更近了,我通过咨询一次次复盘在过往经历中的想法和感受。我重新回望了自己的内心。它令我感觉到我的一切想法,甚至一切行为,不管它有多么黑暗,多么骇人,都有人可以看见并接纳。
但同时,随着一次次的咨询,我越来越知道:我的问题,不管它是“抑郁症”,还是“空心病”,如何面对和解决它们,我能依靠的,只能是自己。
我们都知道,人类有很强的求生欲,但我们常常忽略的,是人同时也有求死欲。当我沉浸在失去生命动力的状态中时,我固然是痛苦的,但同时,我又有一种明确的感觉:那种想要失去生命动力的状态,换句话说,那种像死了一样的状态,实际也是我自身欲望的一部分。
我想起大学的时候读Jim Morrison的传记《此地无人生还》,他提及自己在染上毒瘾时有类似的感受:他知道吸毒在毁掉他,可是他有一种要毁灭自己的欲望。弗洛伊德在研究后期提出过“求死本能”的概念。每个人在活着的同时,又在盼望着死去。何以如此?弗洛伊德的说法是,人类的生命本源由有机分子进化而来,在成为人类以前,我们只是漂浮于宇宙中的微小颗粒,或者说,我们并不真的作为人而存在,而人的求死本能,正是一种想要回归生命源头的欲望。只有死亡,才能将我们从生之欲望、生之枷锁中解放出来,回归宁静无我的状态。
抑郁情绪,生无可恋的感觉,就是求死欲在起作用。这种求死欲,人人都有,只不过,有人把它压抑到了潜意识深处。求死欲,有很多种表现方式。它不是简单表现为人会求死自杀,也可以作用于他人与外界,让人有毁灭他人的冲动。而当求死欲作用于自身的时候,因为会遭遇到同样强烈的求生欲,它最常见的表现方式,往往演变为对生活的逃避。
在广场舞里,她们得以暂时从自己的生活里逃出来。
回想一下夏日广场上,沉浸在广场舞中的大爷大妈们,脸上幸福沉醉的表情,那实际是他们在享受人生终止的时间:他们得以在舞蹈中暂时忘却自己的现实人生,逃离到一个并不真正存在的时空当中。电影,也是人类的逃避本能在起作用。当我们在漆黑的电影院中,将自己投入那闪光的银幕中上演的喜怒哀乐,我们沉醉的,也是我们得以逃离到别人的人生里歇息片刻,而不必跟自己的存在与生活待在一起。
逃避现实,逃避生活,逃避生命。这种逃避几乎随处可见,甚至,整个人类艺术,就是这种逃避本能、求死本能的阐发。因为人有逃离现实的本能,才会创造出迸发无穷想象力的绘画、小说与音乐。人类进而可以通过艺术,构建一个区别于现实的想象世界。
3
如何与“无意义感”共存?
好,那么我们面对的困境实际是:我们存在着,但同时我们又总想不存在。
所以我们才总想给自己的存在找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即意义。我们免不了要去思考,我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拿到了五花八门的答案。我们读书,思考,看周围的人如何生活。
我曾经在世俗意义上给了自己无数答案。比如说,为了自己的存在能让世界变得美好一点点。沿着这个路子下去,我大概会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者,我要找到自我价值,完成自我实现。又或者,我可以为了更具体的原因活着:为了那些我爱的和爱我的人。可是每一个答案,都没能持续。它们都经不住刨根究底地追问。
我还遇到了宗教。读大学的时候,有段时间我常常收到学校里的基督徒在校门口发放传单,邀请大家去参加讲经会、唱诗班。那时候我结识了很多基督徒,常常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周末和圣诞,会去教堂跟大家做礼拜,唱礼赞祈祷歌。那些经文、歌词曾给予我巨大的安慰。当你安静地、缓缓地说出:主啊,请你怜悯我,看顾我,请你倾听我的祈祷;当你跟着大家一起轻轻地唱:如果我的信心软弱了,求神加添;求你听见我心中的呼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神帮助。这些词句、仪式本身就可以给予人巨大的力量和安慰。我曾经在某些深夜,感觉自己真的可以信。但最终,我还是无法信。
我当然也遇到了哲学。从泰勒斯到奥古斯丁,从苏格拉底到笛卡尔,从克尔凯郭尔到加缪,从叔本华到尼采,每一个哲学家似乎,也当然离不开对“意义”问题的探讨。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无数思考的视角和路途。有很多时刻,他们的思考是开创性的、如同灯塔一般珍贵的、令人震颤的。但是最终,他们也很坦诚地告诉我们,这些都并不是最终的“答案”。#p#分页标题#e#
到最后,关于“意义”的寻求,其实变成一种选择。每个人必须选择,自己要走哪条路。这个选择,依靠的不仅仅是理性,还有感性、直觉与勇气,甚至那么一点混不吝的盲目。
坚定地认为活着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赋予它意义,同时“克服”了求生欲,“臣服”于求死欲的人,就选择了自杀。而大多数人,要选择自己与“无意义感”共存的方式。不同的人,对荒诞感、无意义感的感受力与承受力不同。许多人在人生的大多数时候,并不会经受荒诞感、无意义感的折磨,而能够将大部分精力与能量放在专注地展开自己的现实生活上。假如我们对现实生活还抱持着难以割舍的热情、欲望与眷恋,那么每时每刻地投入到生活的洪流中,其实是一种最明智、最高效的方式。所谓“对未来最大的慷慨,是把一切献给现在。”
但绝大多数人,不可避免地,总会在某些时刻与“无意义感”狭路相逢。甚至对某些不幸(又或者是幸运)的人来说,他们终其一生,要时刻接受“无意义感”虎视眈眈的注目礼。
有人的解决方式是,认清“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之后,坦然接纳这个事实。然后,或者在无意义中向死而生,创造自己的意义;又或者,彻底放弃对“意义”的寻求,认为人可以不必寻求意义,只是单纯地存在。如果真能如此,那是皆大欢喜的。但我并不相信人可以真的如此,对“意义”的寻求是内化在人类这个概念之中的,甚至,为了活着而活着,这个理念本身就是对意义问题给出的答案。也有人在经历了所有怀疑之后,主动选择将自己对意义的寻求交付给宗教。基督教是一种最令人安慰的交付对象,假如真的能交付的话。
还有的人,在现有的宗教、哲学、观念体系中,也就是以上的所有可能性中,无法被任何一种说服,也无法甘愿选择任何一种去相信。那么我的方式是,容许自己在怀疑的泥沼中再待一段时间,哪怕这个“一段时间”会是一生。但我会提醒自己,在虚无面前,要有足够的谦卑:或许我对宇宙或人生根本一无所知。或许我像偏执狂一样执着的真相是:有意义与无意义一样,真相与假相一样,存在与不存在一样。或许这个真相是以人类的能力无法理解的。又或许,根本不存在真相。
剧作家贝克特写过这样的话:“你必须前进。我无法前进。但最终我会前进。” 我意识到,我可能终其一生,会在这三句话里无限循环。但也正是因着这谦卑,我愿意,全神贯注地,待在这个循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