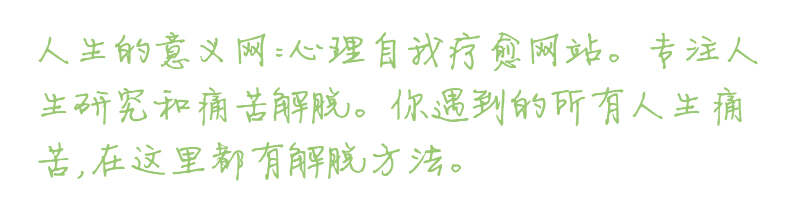弗洛姆:《现代人的反思》第2节病态的人格和病态的生存方式“现代人的特征
2016-10-09 16:38:43 发布:人生的意义网

作为人道主义的哲学家,在他看来,现代人之所以陷于灵魂空虚、孤独不安的“无我”状态,就在于现代人的生存的目的违背了真正的人性及需要,就在于现代的社会造就了病态的人格。因此,弗洛姆从人的存在情境出发,从现代社会的结构入手,揭示造成现代人病态生存方式的原因,以便为迷茫的现代人找到一条出路。
一、人的存在二律背反和历史的二律背反
弗洛姆遵循西方人本主义的传统,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具有理性,这是人自身独有的特性,它弥补了人与动物相比缺乏调节的本能以适应变化的局限,借此人类从自然界所有生命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不过弗洛姆并没有仅仅停留于此,他进一步指出了理性对人的双重作用,理性像一把双刃剑,它既让人享有了“万物之灵”的尊严与骄傲,又让人品尝了具有自我意识的痛苦与孤独,理性是人的福分,又是人的祸根,正是理性使人产生了存在的二律背反。
弗洛姆认为人的存在的二律背反源于人类的起源,源于人与自然的分离。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遵从自然的法则,且无力改变这些法则;”自然界是人类的故乡,是生命的萌芽繁衍地,是人类没有痛苦的伊甸园。另一方面,人又超然于自然的其他部分,当他拥有自我意识、理性和想像力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成为“宇宙的反常物”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天然和谐,从而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而人一旦与自然分离,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永远地丧失了与自然的一体性,再也无法回到与自然相和谐的状态。“人一旦被逐出天堂,脱离了与自然浑为一体的原始状态,天使就手执烈焰宝剑挡住了寻归者的归途。”人成了永恒的流浪者,自然成了人永远也回不去的故乡,是人类不归路上一个越来越远的起点。
人与自然的天然和谐被永久地打破,人的存在与生俱来伴随被逐出.伊甸园的痛苦,这是人性的分裂,也是人存在的特征,是人永远无法解决的存在的二律背反,是人痛苦的最终根源,“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生存所固有的矛盾。”而生与死,潜能与实现,孤独与合群的生存的二歧性,又以更具体更直接的方式加重了人类的痛苦。
生与死的矛盾是人的生存的二歧性的首要表现。人类虽然凭借理性成为万物之灵,成为自然界中惟一认识到自己会死并由此烦恼痛苦的动物。面对这一躲不过去的厄运,他明白到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他的存在是有限的,“除了接受死亡这个事实外,我们对此没有任何事情可做”。
人的生存的二歧性的第二个方面表现,便是人所具有全部潜能却因生命有限而不能完全实现的矛盾,这是对人类的另一致命性打击。“人之情境的悲剧性在于自我的发展永远不会完成,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人的潜能也只能得到部分的实现。人总是在他还未充分诞生前就死亡了。”
生存的二歧性的第三个方面表现便是人的孤独与合群的矛盾。作为人类的整体,人在大自然中是孤独的,“万物之灵小.宇宙之精华,,的特性注定了人与万物的不同,也注定了人的孤独。可人作为生命存在的一种,他又必须与所有的生命共栖于宇宙中,他不能离开其他的生命而独立的存在。这形成了人既要寻求与他人的接近,又要寻求独立,既要寻求与他人结为一体,同时又要维护他的惟一和特殊性的孤独与合群的二律背反。
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许多历史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既可在它们产生时加以解决,也可在人类历史的随后阶段给予解决。”弗洛姆举例说,现代社会存在的“有丰富的用于物质满足的技术手段与无能力将它们全部用于和平及人民福利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历史的二律背反,然而它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和无法解决的矛盾,它是由于人缺乏勇气和智慧所产生,也将随着人的勇气和智慧的提高而消除,因为这类矛盾不是人生存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随着历史的发展,当人类平等的物质基础具备时,人们便可以借助自己的行动,寻找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来消除这种矛盾。
由此历史的二律背反的特征便在于它不是人类不可避免、不可消除和解决的矛盾,那种有意将历史的二律背反和人的存在的二律背反故意混淆的做法,其目的只是在于推行“不应该是就不能是”而顺从命运安排的消极的宿命论观点。不过弗洛姆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企图并不足以使人放弃解决这些矛盾的努力。原因在于“人之精神的一个独特性就在于,当人面对矛盾时,他不会无动于衷,他会逐步树立起解决这一矛盾的目标。人类的所有进步就是源于这个事实。”
当面对存在的二律背反时,人类并没有选择“力图退回到人类以前的存在方式中,消灭人所具有的理性和爱的特性”的方式,而是接受存在的现实,接受挑战。人既然踏上了与自然分离的不归路,他只有被迫继续前进,必须通过不断的努力,战胜这种内在的分裂,既为自己的存在说明存在的意义,又为消除人与自然、与他人的分离找到相统一的更高形式来达到新的平衡与和谐。
人类凭借自己独有的理性,不断努力,充分发展他具有的人性的力量,创造了属于人类自己特有的世界:他通过神话幻化出无所不能的神与英雄,显示出人统治自然的渴望和决心;他通过宗教的灵魂不死,以对抗现实中人的生命注定死亡的悲剧事实;他通过科技不断满足人日益丰富的物质需要,从而提高人的生存质量;他通过艺术,沉浸在美的追求中,以便保持灵魂的安宁与祥和;他通过哲学形而向上的追求与冲动,表现了人对有限到无限,从已知到人生的意义网,从缺陷到完美的渴望与向往。“人把生命的赌注押在宗教、政治、人道主义理想上,这些追求构成并表现了人之生命独特性的特征。的确,“人并不仅仅为了面包而活着”。因为“人太致力于一个目标,一种观念、或一种超越人的力量(如上帝),是人在生活过程中追求完整之需要的一种表现。因此,自然的伊甸园固然一旦失去便不可复得,但人却用理性,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了一个人类的新家园,一个属于人自己的世界,使自身安归其家,从而为人类的存在展示了独有的凄美和壮丽,抚慰了人类存在痛失自然家园的痛苦。人类的历史便是在抵制或减缓人的存在的二律背反,消除历史的二律背反中不断前行,终于在工业文明的鼎盛时期,听到了人类发自内心的欢笑,在社会进步中,感受到人之力量的伟大与自豪。
20世纪的战争与危机,转瞬之间击毁了人类千百年来所拥有的美好的期望,摧毁了人为克服存在的二律背反做出的种种努力,人类陷入了比他诞生之日痛失自然家园的苦难更深的悲哀之中,因为人类独有的家园又一次岌岌可危,干百年的努力有可能付诸流水。对此困境,弗洛姆认为,造成伟大幻想破灭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从人之存在的二律背反中,找出真正的人性及需要。以弗洛姆之见,面对人之存在的二律背反,只有一种办法可以从根本上释放人的存在的痛苦,那便是"面对真理:承认在毫不关心他命运的宇宙中,他的根本孤独和寂寞;认清对他来说,超越于他并能解决问题的力量是不存在的。人必须承认他对自己负有责任,而且,他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即只有运用他自己的力量,才能使他的生命富有意义。”“人除了通过发挥其力量,通过生产性的活动而赋予生命以意义外,生命并没有意义。只有时刻警惕,不断活动和努力,才能使我们实现这一任务,即在我们的存在法则所限定的范围内,充分发展我们的力量。人绝不会停止困惑、停止好奇、停止提出问题。只有认识人的情境;认识内在于人的存在之二律背反,认识人展现自身力量的能力,人才能实现他的使命:成为自己、为着自己、并凭借充分其才能而达到幸福。”因此,人的真正需要就是发挥自己的潜能。
二、病态的人格和病态的生存方式
不仅如此,弗洛姆更进一步地分析和指出造成现代人没有看清人的真正幸福和的症结在于推动实现潜能的动力系统——性格呈现出病态,病态的人格造就出病态的现代人,病态的现代人造就出病态的社会。弗洛姆尖锐地指出:“人都具有人的情境和内在的存在之二律背反,这一点是共同的;但他们在以特殊的方法解决人的问题方面,却是各具特色的。人格的无限差异,其本身就是人之存在的特征。”
在性格上,弗洛姆既不同意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把性格当做行为特性,定义为“一个个体所有的行为形式”,也反对弗洛伊德用性驱力来解释性格特性的动力性,把各种不同的性格理解为各种性驱力形式的升华或反馈,弗洛姆认为性格的根本基础并不在各种类型的里比多中,而是在特殊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在生活过程中,人通过两种过程,其一,同化的过程获得并同化事物,其二,使自己与他人(及自己)有关而使自己与世界发生着联系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形成一个借以使自己与他人与世界发生联系的特定的联系形式,从而体现出其独有的性格。藉此,弗洛姆把性格定义为“把人之能量引向同化和社会化过程的(相对固定)形式。
在弗洛姆看来,性格在人的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赞同“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的古老的名言,认为人之特征及不可改变的最深层的习惯和意见是性格结构的产物,思想和判断也是性格的产物。性格既有选择人的观念和价值的功能,也具有选择与其性格相一致的生活方式的能力,是人适应社会和生存发展的基础,因此,健康的性格是人发挥潜能达到幸福的关键所在。弗洛姆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解剖,认为有四种病态的人格导致了现代人的危机与迷茫。
第一种,接受型的人格。接受型人格的人的生活信念是“一切好的都源于外界”,因而将接受外界的来源视作获得物质、慈爱、爱隋、知识和快乐等的惟一途径。这种人毫无主见,事事依赖他人,从不主动出击,一味被动接受;在思想上,这种人是最好的听众,一味地接受观念而从不产生观念;在知识上,从无创造性,从不愿意努力去探索知识的奥秘;在爱情上,遵循等待的惯性,从不主动去爱别人;在社会上,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个魅力的帮助人或一个崇拜的偶像,作为自身的依靠,以获得安全感和依赖感;在家里,事事依赖父母,从不反馈回报别人;在日常生活中,极其爱好吃喝,……总之,被动地接受、十分地依赖是这类人的典型特征,思想的怠惰,判断力的萎缩,毫无自己的见解与主张,缺乏生命的进取与活力,便是这类人的真实写照。
第二种,剥削型的人格。剥削型的人格和接受型的人格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一切好的东西都源于外界,不管需要什么都要到外面寻求,而不依靠自己的创造。不同的是,他不像接受型的那样被动地坐等他人的恩惠,而是通过强力或狡诈,想法设法巧取豪夺他人的东西,剥削和掠夺是这种人格的典型特征,贪萝、巧诈、猜疑、妒忌是这类人的脸谱,由于无休止的占有欲和掠夺欲使这类人整日处在忧虑烦恼之中,内心得不到片刻和快乐。
第三种,囤积型的人格。与前种相信一切可以从外界获得的人格类型不同,囤积型的人格不相信有可能从外界获得任何新东西,他们的座右铭是“世上没有任何新东西”,因此,他们用囤积和节约建立一堵自我保护的安全墙,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地把东西带进来,而尽可能少地把东西带出去。这种人是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是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
第四种,市场型人格。市场型的人格是随着近代商品与市场发达而产生的,这一类人视一切为商品,以价格高低衡量事物,.包括品德学问,追求把自己在市场上成功地推销出去。这一类人投机应变,虚无冷漠,毫无个性,孤独软弱,从不真正关心他人的生命和幸福,整日生活在压力之下,惴惴不安。
弗洛姆指出这四种人格是典型的理想化状态下的分析,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很少是绝对的单一的典型人格,而是几种的混合,只不过看哪一种倾向占统治地位而已。不仅如此,从历史的演进来看,不同的性格结构的地位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也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譬如,十九世纪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性格结构是囤积型和剥削型倾向,而二十世纪则是以市场人格或叫商品性销售人格为主。然而不管怎样,它们都是一种不健全的人格,这一点是毫不质疑的,病态的人格违反了人的真正的本性及需要,导致了失去个性、空虚孤独、生命无意义和个体自动化等弊病及后果。弗洛姆在分析病态人格的基础上,又把聚焦点关注于现代西方社会,在他晚年总结性的著作《占有与生存》中,进一步揭示了由病态人格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而产生的一种病态的生存方式,即占有的生存方式,从而把病态的人格理论进一步深入化。
弗洛姆认为存在和占有是人性固有的两种生存欲望,是人对生活的两种根本不同形式的体验。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哪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而现代的社会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利润和强权这三大支柱之上,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的判断带有极大的偏见,捞取占有和获利是生活在工业社会中的人,不可转让的天经地义的权利。
占有感的一个最重要的对象就是自我,“自我包括许多东西,我们的躯体、名利、社会地位、我们的占有物(包括知识在内)以及我们自己产生的并想要将其传道给别人的想法和观念,自我是现实的物质(如知识、技能)与围绕着某一现实的核心而形成的某些虚假的物质的混合,重要的并不是构成自我的内容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觉得自我是一个我们占有的物,而这个物又是我们体验自我个性的基础。”
占有最典型的一种表现形式即是消费,它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另一方面又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即减轻了人的恐惧心理。现代的消费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我们占有的和所消费的东西即是我的生存。”思想、观念、信息、知识、习惯成为一种占有物,成为个人财产的一部分。占有欲像无孔不入的空气充塞着整个社会,占有从外在的需求变为人内在的性格,主宰着人的行动,可是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并没有使现代人感到幸福,反而带来严重的后果。弗洛姆犀利地指出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和以财富利润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必然会产生对强力的要求,诉诸于暴力和强权,既要保护自己占有的物,又要千方百计地掠夺别人的物。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对于一个人来说,幸福就在于他能胜于别人,在于他的强力意识以及他能够侵占、掠夺和杀害他人。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的人缺乏安全感和快乐感。
最为可怕和严重的是,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在我与我所拥有的东西之间没有活的关系,我所有的和我都变成了物。丧失了生命活力的占有,尽管占有的物越多,却越来越使自己被更多地物化,越来越使生命力僵滞,人变成了追逐占有物的不停的机器,越来越不快乐,而这些与人的真正本性与需要恰恰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