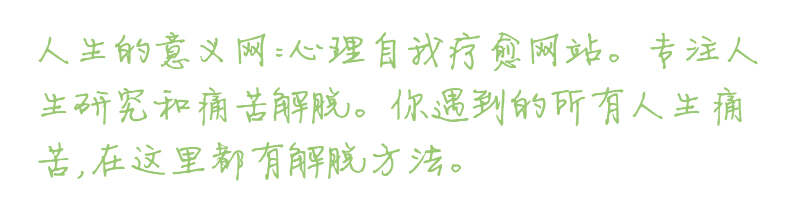邓晓芒:欧洲虚无主义及其克服——读海德格尔《尼采》札记

海德格尔在其一千多页的煌煌巨著《尼采》中,以及在收入到《林中路》的“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文中,反来复去谈论的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欧洲虚无主义的问题。
海德格尔如此热中于谈虚无主义,当然不是为了赞扬它,而是为了克服它。正如胡塞尔谈“欧洲科学的危机”(或欧洲人性的危机)一样,海德格尔也把克服欧洲虚无主义视为当代的一种“急需”(Not)。他之所以关注尼采的思想,正是因为在他看来尼采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虚无主义者。
从尼采身上,他看出欧洲虚无主义来自于西方形而上学,尼采对欧洲虚无主义的批判就是对西方整个形而上学的批判;而正由于尼采从虚无主义的立场批判形而上学,所以尼采本人也陷入了形而上学,成了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
海德格尔则想借尼采这一实例,阐明他自己的一个创新思路,即力图通过克服西方形而上学来克服虚无主义。本文将考查海德格尔这一努力的理论依据和客观效果,并分析海德格尔在基本思路上的偏颇。
一、什么是欧洲虚无主义?
根据尼采的说法,“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海德格尔也同意这种定义,认为“虚无主义是一个过程,是最高价值贬黜、丧失价值的过程。”[1]不过,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定义还不足以穷尽虚无主义的本质,因为它并没有回答什么是价值或最高价值的问题,而是把价值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在海德格尔看来,“虚无”是和“存在”相对而言的,尼采却忽视了价值后面的“存在”思想:“‘虚无主义这个名称和概念指的是一种存在思想,但尼采却完全是从价值思想出发来把握虚无主义的。”[2]
海德格尔认为这正是尼采本人没有超出虚无主义的主要原因。所以海德格尔对虚无主义的分析就有两个层次,即一般的虚无主义,以欧洲自古以来的形而上学为代表;以及“古典虚无主义”,以尼采本人为代表。
那么什么是一般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呢?尼采和海德格尔认为,“虚无主义是那种历史过程,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超感性领域’失效了,变得空无所有,以至于存在者本身丧失了价值和意义。”[3]这里的关键在于对“超感性领域”的设定,因为它涉及到西方形而上学的起源,即在柏拉图那里对现实世界和超感性的理念世界的划分。
在尼采看来,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一个超感性的价值世界,即以最高的“善的理念”为统治者的彼岸世界。“对最高价值的设定同时也设定了这些最高价值贬黜的可能性;而当这些最高价值表明自己具有不可企及的特性时,它们的贬黜也就已经开始了。生命因此就显得是不适宜于这些价值的,根本无能于实现这些价值。因为这个缘故,本真的虚无主义的‘预备形式’就是悲观主义。”[4]
这里有个明显的逻辑漏洞,即:最高价值的设定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它的贬黜,因为之所以要设定“最高”价值,正是着眼于它不会、或者最难遭到贬黜,因而正是想要避免虚无主义。它固然不能保证自己不被贬黜,但它的遭到贬黜显然不是由于它的设定,而是另有原因。
当然,如果怀有一种先入之见,即认为根本不存在任何最高价值,这就不算什么漏洞。因为在此前提下任何最高价值都是一种伪价值,伪价值总有一天要被识破,而现实生活的价值又早已被淘空,这就会使那些相信伪价值的人(基督徒)陷于绝望和一无所有,从而导致虚无主义。但这一先入之见的前提本身正是某种虚无主义。
海德格尔看出了这一点,他引用尼采的话:“虚无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对于如其所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不应当存在;对于如其应当所是地存在世界,他断定它并不实存”,并评论说:“在这里,尼采倒是用一种双重的否定绝对地否定了一切:首先否定了现存世界,进而同时也否定了从这个现存世界出发值得愿望的超感性世界,即理想。”但尼采这种虚无主义不同于以往的虚无主义,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虚无主义:它背后“已经潜伏着对这一个世界的惟一肯定,它拒斥以往的东西,靠自身来建设全新的东西,而且不再认可一个自在地存在的超世界”[5]。这就是其所谓“一切价值重估”,它否定了一切以往的价值,但却确立了自身的强力意志的绝对价值。
所以,尼采是从他自己的虚无主义的立场来给以往的虚无主义下定义的。在他看来,柏拉图对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划分奠定了后来西方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石[6],当一切价值都被归于上帝的最高价值时,人生的现实价值就被淘空了。人之所以要把他自身的价值全部归于上帝,是因为他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不了这些价值;而他之所以实现不了他的价值,则是由于他缺乏“强力意志”,因此他就通过某种“人化”的方式使一个对象获得最高价值,而设定了一个拥有所有这些价值的上帝来供自己谟拜。
“人作为诗人、作为思想家、作为神、作为强力:呵,他把何种君王般的慷慨大方赠送给事物,为的是使自身贫困化并且使自己感到可怜!迄今为止,他最大的无自身状态就是,他赞赏、崇拜,而且懂得如何对自己隐瞒以下事实:他就是创造所有他所赞赏的东西的人。”[7]
海德格尔则把这种缺乏强力意志的“幼稚性”归结为,人们没有意识到“那种按照人的形象并且通过人对世界的设定,乃是所有世界解释中惟一真实的方式……。以往的最高价值之所以能够获得它们的地位和效力,是因为人把自己设定为事物的意义和价值尺度,但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而倒是坚持认为:他所设定的东西是事物的一个赠品,是事物自发地带给他的一个赠品。”[8]这些说法与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对基督教的批判如出一辙[9]。神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的本质,上帝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不过,海德格尔不像尼采那样,把这种“幼稚性”归因于某种偶然性,而是视为存在的“命运”。因为在存在自身的展开中,“必须有一种价值被置入存在者整体之中,人的自身价值才能得到保障;必须有一个彼岸世界,人才能忍受此岸世界。”[10]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存在命运是新老虚无主义者都避免不了的,只要他们还停留于主体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上。“作为形而上学,它们自始就让存在本身的真理处于未被思考的状态。但作为主体性形而上学,它们却使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变成表象和预先设定的对象性”,因此,“人是把这种超越者当作它的宗教主体性的天命(Vorsehung)来加以严肃对待,或者只是把它当作他的自我中心的主体性的意志的托词,都丝毫不影响人类本质的这种形而上学的基本态度的本质。”[11]
就是说,存在要敞开自身,首先必须在形而上学中遮蔽自身,进入到存在者和存在者之间的关系;而存在的这种被遗忘、被忽略和被“悬搁”(εποχη),其实是存在本身的“自行抑制”[12]。的确,我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看到,当他宣称要研究一门“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时,他实际上只是在考察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或者说,在他看来要研究存在就只有通过研究存在者,因而存在者就是他所理解的存在本身。这是一种混淆,但这种混淆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倘若没有这种混淆,那就没有西方形而上学,也就不会有供尼采所批判的欧洲虚无主义,而这样一来,就连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本真意义的问题也提不出来了。
所以海德格尔提出了这样一种类似悖论性的命题:“虚无主义本质关涉到存在本身,更准确地说,存在本身关涉到虚无主义的本质,因为存在本身已经进入历史中了,即存在本身在其中一无所有的历史。”[13]存在本身进入了它在其中一无所有的历史,但既然它在其中“一无所有”,又怎么能够说它已经进入了历史呢?进入了不就是已经“有”了吗?海德格尔不屑于用黑格尔式的“历史辩证法”来解开这一悖论,所以我们也只好暂时忍着,且看他下面怎么说。
二、以毒攻毒:尼采的反虚无主义的虚无主义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古典的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的完成”[14],是一种最彻底的、意识到自身的虚无主义。对于尼采来说,只有这种极端的虚无主义才有可能克服虚无主义,因为,“虚无主义不能从外部来加以克服。仅仅用另一个理想,诸如理性、进步、经济和社会的‘社会主义’、单纯的民主之类的东西,来取代基督教的上帝,从而试图把虚无主义强行拆毁和排除掉——这样做,是克服不了虚无主义的。”[15]反之,只有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将过往一切形而上学所追求的价值、因而将形而上学本身加以颠倒,用“强力意志”这种“主人的道德”取代生命力萎缩的“奴隶道德”,才能克服虚无主义。“尼采把他的形而上学理解为极端的虚无主义,而且,这种虚无主义同时不再是虚无主义了。”[16]为什么不再是虚无主义了呢?因为尼采把与虚无相对立的存在理解为“价值”,因而把虚无主义理解为最高价值的失落,而把对虚无主义的克服理解为价值的重建:“一切价值重估”。正因为重建了一种新的价值,即“强力意志”,所以它虽然是对一切自在的价值的毁灭,但却是对一种动态的、人为的价值的恢复,这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绝对价值。我们在这里似乎可以看到黑格尔“主体即实体”和“真无限性”原则的影子,的确,海德格尔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把尼采和黑格尔的思想相提并论,统称为“主体性的形而上学”[17]。
由此可见,尼采是以一种“以毒攻毒”的方式来克服欧洲传统的虚无主义的,他以一种新的形而上学颠覆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在他看来,“目的”、“统一性”、“真理”这样一些概念,作为彼岸世界的自在的价值,都是骗人的,都是对人的生命的此岸价值的抽空。尼采的颠覆就在于,公开宣布“上帝死了”,不再用任何自在的价值来衡量此岸世界的事物,而是就在此岸世界中凭借生命的强力意志创造出自身的价值来。这种创造是永不停息的,而且是“加速度”式的,因为“只有当强力保持为强力之提高,并且受命于‘强力之增加’,强力才是持久的强力。即便只是中断强力之提高,只是停滞于某个强力等级上,也已经是强力之下降的开始了。”所以它只能是“求意志的意志”[18]。强力意志的这样一种“永恒轮回”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轮回,而是在一个永远上升过程中的轮回;而之所以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并不是说创造出来的东西完全相同,而是着眼于不断的创造、创新本身。创造出来的东西本身没有价值,或者说,任何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是该毁灭的,只有同一个创造本身是永恒的[19]。
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的这种“以毒攻毒”是非常深刻的,它不但揭示了欧洲虚无主义的源头,而且暴露了这种虚无主义的本质。欧洲虚无主义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虚无主义,反而自认为自己是立足于坚实的存在论(本体论)基础上的;然而,正由于它的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它实际上从来没有思考过存在本身的问题,而只是考虑存在者的问题,而这样理解的存在者,哪怕是存在者整体,都恰好是无根的,因而是虚无的。但海德格尔同时也指出,尼采自己虽然揭示了欧洲虚无主义的这一存在论上的本质,却并没有理解这种本质,因而他也无法真正克服虚无主义。关键就在于,尼采把存在仅仅理解成了“价值”。“存在成了价值。……由于存在被尊为一种价值,它也就被贬降为一个由强力意志本身所设定的条件了。只要存在一般地被评价并从而被尊奉,则存在本身先就已经丧失了其本质之尊严。如果存在者之存在被打上了价值的印记,并借此就确定了它的本质,那么,在这一形而上学范围内,即始终在这个时代的存在者本身的真理的范围内,任何一条达到存在本身之经验的道路就都被抹去了。”在这里,“存在沦为一种价值了。从中表明,存在并没有得以成为存在。”[20]
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对欧洲虚无主义的批判并不彻底,他只揭示了对超验的最高价值包括上帝的最高价值设定的虚假性;但其实,即便不考虑这种虚伪性,单是设定一个最高价值,甚至单是用价值的眼光来看一切存在者,这已经就是虚无主义了。“虚无主义不只是最高价值之贬黜的过程,也不只是对这种价值的抽离。把这些价值安插入世界中,就已经是虚无主义了。”[21]因为这种做法撇开了价值的来源即存在,而把价值本身当作终极的根据。
海德格尔问道:“价值思想来自何处?那种根据价值来评估一切、把自身理解为一种价值评估并且以一种新的价值设定为己任的思想来自何处?尼采本人已经提出了关于价值思想的来源的问题,也已经对之作了解答。……回答是:来自人的意志,即人要为自己谋得一种价值的意志。但如果人所归属的世界本身并不具有某种价值、某种意义和目的、某种统一性和真理性,如果人并不隶属于某个‘理想’,那么,他如何能为自己谋得一种价值呢?”[22]就是说,强力意志要设定某个价值,仍然还是要放在这个世界中来设定,至少,一个人强力意志的大小,要看他的意志在这个世界中实现出来的大小,这就仍然不能脱离这个世界中的统一性、真理性尺度,不能脱离针对这个世界而设立的目的。一种力只有通过其作用效果才能衡量[23]。强力意志的本质就在于“对强力之提高的预计,对各个强力等级的强势作用的预计”(“预计”即Rechnen,或译“算计”)[24]。因而,价值不单单与人有关,而且与世界有关,与“存在”有关:“虚无主义的本质根本就不是人的事情,而倒是存在本身的事情”[25]。但恰恰这一点被尼采遗忘了,他只想到要教人成为“超人”,而没有从根本上思考存在之为存在。
于是,海德格尔把尼采未能克服虚无主义的原因归结为,他仅仅立足于价值的立场,试图用一种新价值的创立来代替旧价值。“尼采关于虚无主义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概念。尽管有种种深刻的洞见,但尼采没有能够认识到虚无主义的隐蔽本质,原因就在于:他自始就只是从价值思想出发,把虚无主义把握为最高价值之贬黜的过程。而尼采之所以必然以此方式来把握虚无主义,是因为他保持在西方形而上学的轨道和区域中,对西方形而上学作了一种臻于终点的思考”,他没有看出,“在价值概念里潜伏着一个存在概念”[26]。不过,海德格尔也不认为尼采根本就没有思考存在之为存在,他说:
“我们现在所做的沉思往往会产生一种嫌疑,仿佛我们对尼采思想作了一个假定:它必须从根本上思考存在之为存在,但却耽搁了这种思考,因而是不充分的。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意思。而毋宁说,我们要做的事情仅仅在于,出于对存在之真理问题的思索而深入到尼采形而上学中去,为的是基于对他的思想的至高忠实去经验他所思的东西。”[27]
这段话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海德格尔当然是在批评尼采,认为他的思考还“不充分”,还不足以克服欧洲虚无主义。例如在几页以后他就批评尼采说:尼采的“价值之思现在就被提升为原则。存在本身作为存在原则上是不被允许的。在这种形而上学中,按其特有的原则来看,存在就是一无所有的了。在这里,随着存在本身一道,如何还能出现值得思想的东西,亦即作为存在的存在呢?”“照此看来,尼采的形而上学就不是一种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它乃是向虚无主义的最后一次卷入。通过那种根据强力意志而进行的价值之思,尼采的形而上学仍然保持着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承认,但由于把自身束缚于一种对作为价值的存在的解释,它同时也囚于一种不可能性中,甚至不可能把一道疑问的目光投向作为存在的存在。”[28]
虽然海德格尔想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点而完全抹杀尼采在克服欧洲虚无主义方面的功劳,因为当他要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的时候,他毕竟启动了通往存在之路(虽然他自己重又堵塞了这条通路),“就此而言,尼采恰恰就在思考存在”[29]。然而,即使如此,“尼采是不是也已经承认了存在者之存在,而且也承认了它自身,即存在,也就是存在作为存在呢?绝对没有。存在被规定为价值,从而——根据存在者——被解释为一种由强力意志(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所设定的条件。”[30]尼采仍然只是局限于在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这个视野中讨论存在问题,也就是局限于在形而上学的视野中讨论问题,用存在者(价值、强力意志)取代和遮蔽了存在本身。总之,尼采并没有克服虚无主义,他仍然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并且和柏拉图一样是一个形而上学者。
那么,如何来思考?海德格尔认为,不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回存在来,而是就在虚无之中即可以看出存在。“存在不是在某个地方孤立地隔离的,此外还悬缺着;而不如说,存在之为存在的悬缺乃是存在本身。在悬缺中,存在本身与它自身一道掩盖自己,这种向着自身消失的面纱(存在本身就是作为这种面纱在悬缺中本质性地现身的)乃是作为存在本身的虚无。”[36]虚无就是存在,但由于对存在的遮蔽和悬缺(缺席),虚无就成了虚无“主义”;不过这种遮蔽和悬缺也正是存在本身“现身”的方式,存在本身凭其“自我坎陷”(借用牟宗三语)显示了它自身的威力;问题是我们不能把这种威力当成就是存在本身,而必须设想:“存在,作为存在被思考的存在,不再能够被叫作‘存在’了。存在之为存在是一个有别于它本身的东西,它如此确定地是另一个东西,以至于它甚至不‘存在’(ist)”[37]。
这里明明是黑格尔的思想:纯存在就是纯无,存在本身就是存在的自我否定,即虚无。但海氏却不愿意“辩证的”来看这个问题,而要“从实事来看”,即把存在看作在历史中通过它的自身隐匿而本质性地现身的过程。尽管在这种历史中,“存在本身是一无所有的”,而且“存在本身就一直是未被思考的”[38],但存在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启发我们从中追问和思考存在本身,也就是追问这种虚无主义的历史的本质。“本真的虚无主义的本质乃是在其无蔽状态之悬缺中的存在本身,这种无蔽状态作为存在自身的‘它’(Es)本身而存在,并且在悬缺中规定着它的‘存在’(ist)。”[39]这也正是海氏不愿意承认他对尼采的“不充分”有所批评的真正原因,海氏不愿意人们认为他离开了尼采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而另外建立了一套新的形而上学,其实他只不过是回到了主体性的形而上学的发源地而已。
不过,当我们通过存在本身的自我否定来思存在时,我们所思的毕竟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存在本身了,因为它已经被纠缠进或者说“卷入”到了存在者之中。所以海德格尔说它已经“不再能够被叫作‘存在’了”。在另一处,海德格尔也说:“‘存在’始终只是一个暂时的词语”,并且说:“让我们首先来思量一下,‘存在’原初叫‘在场’(Anwesen),而‘在场’意味着:入于无蔽状态而持存出来。”[40]但是,对“在场”的无蔽状态的“思量”是不是就是对本真的存在之思了呢?显然不是。
海德格尔说:“可是,在已经作为在场而显现的存在中,与其中起支配作用的当前和时间的本质一样,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无蔽状态也同样还是未经思想的”,“只消存在者之存在作为在场状态显现出来之际基于何处这一点还是未经思想的,那么,我们仍然尚未本真地思想。”[41]因为,在场把自己作为存在而显现出来时恰好遮蔽了存在本身,这正好体现了虚无主义的本质,并显现为人的本质[42]。尼采的“强力意志”就是一种“在场”,但它同时又是对存在的遮蔽。海德格尔认为,要想真正“思及”存在本身,必须打消一切想为之“下定义”的习惯,甚至不可能用一个陈述句来表达。“在陈述句的形式中不可能伸手可及地包含着、因而也无法提供出那种关于虚无、关于存在、关于虚无主义及其本质、关于本质(名词的)之本质(动词的)的答复”;而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时,我们就已经为思进行了一种准备或“前观”,这种前观只能以在“存在”上“打叉”的方式来写“存在”[43]。
当然,海德格尔这种自创的标示法(“打叉”)也还只是一种“否定性的收获”,如果不作进一步解释,那么它和康德对“自在之物”的“思”也没有什么区别。在康德那里,自在之物就是只可思维而不可认识的存在,对于现象界的(存在者的)存在论来说,本体界的(作为存在本身的)存在论只能是“打叉”的存在论,只是信仰对象而不是认识对象。而与康德撇开现象来思自在之物类似,海德格尔的目标就是能够做到“不顾存在者而思存在”[44]。但他又解释说:“‘不带存在者而思存在’并不表示,与存在者的关联对存在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可以撇开这种关联不谈了;它毋宁是表示,勿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来思存在。”[45]
海德格尔一方面说,他只是“追问”存在,为追问而追问,而不是针对任何答案,甚至排斥任何答案;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勉强为之地对追问的对象提供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明,以表达出存在的意义。最令人迷惑的表达是Ereigenis这个词。就连对这个词语抱欣赏态度的国内海德格尔专家孙周兴先生都说:“我们也确实地感到,正是在‘大道’[Ereigenis]一词上,体现着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深刻的‘两难’:一方面,海氏力求挣脱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概念方式和学院哲学的言说方式,寻求以诗意语汇表达思想;而另一方面,海氏所确定的‘大道’以及相关的词语,恐怕终究也透露了一种不自觉的恢复形而上学的努力……这里所谓‘两难’,既是‘思’的困惑,也是‘说’的艰难。在语言表达上,后期海德格尔一直处于‘说-不可说’的边缘境地中,苦尝‘无言’的痛苦。而照海氏看,归根到底,‘大道’一词上也是要‘打叉删除’的——‘大道’恐怕根本就不是一个‘词语’。但以上所说,却已经让‘大道’落入‘意思’了。岂不是‘尽入死门’?但又奈何之?”[46]可谓深得其中三昧。
由此可见,海德格尔想通过克服西方形而上学来克服欧洲虚无主义的构想并不成功。其原因就在于,他从本质上没有能够摆脱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如他的老师李凯尔特)的思维模式,即以为可以通过“划界”的方式来设定西方形而上学的限度,从而立于形而上学的背后来对之作一全盘的批判。我们甚至可以模仿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而把海氏的存在学说称之为“纯粹存在批判”。与康德不同的是,海氏通过自己的理论实践也意识到,这种划界不可能是一次性的或一劳永逸的,而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道路”,他所有的理论成果只不过是这条道路上的临时的“路标”;但思维方式上的先天缺陷使他无法实现他的理论抱负,即把西方形而上学引回到它的根源处,以拯救它在当代所陷入的虚无主义的危机。
四、质疑和评论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从尼采的最后的虚无主义(或最后的形而上学)出发,企图通过追溯西方形而上学的源头来克服欧洲虚无主义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切实的实现。实际上,他所设计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即想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预先去为历史上所有已经说出来的东西定位,将本身无规范的东西弄成一种貌似有规范作用的东西;同时却排斥价值论的立场,而想凭借某种本质上仍然是认识论的眼光(“显象学”、“去蔽”“、澄明”)超出传统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又躲躲闪闪,含含糊糊,这就使他的哲学成了一种既不是认识论、又不是价值论,既没有完全成为形而上学、又不是仅仅止于“思想”的东西。他的“道路”仍然只不过是从思想通往(未来)形而上学的道路,而他的“源头”仍然是某种价值论。何以见得?
首先,所谓“克服欧洲虚无主义”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一个价值论的命题。海德格尔提出这一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尼采从价值论出发,认为虚无主义“不好”,须要克服;海德格尔从存在论出发,认为虚无主义“不对”,也要克服。但我们可以反问:虚无主义怎么就“不对”了?何以得知虚无后面一定“有”一个“存在”?如果说西方两千年来“遗忘”了作为存在的存在,那么我们不是同样可以说,西方人两千年来也遗忘了作为虚无的虚无?何况就欧洲的情况来说,后一种说法可能比前一种说法更真实。
例如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谈到“存在”(“有”)的哲学时他举了巴门尼德的例子,而在谈到“虚无”(“无”)的哲学时就只能从东方找例子,如“佛教徒”[47]。其实除了佛教徒外,中国古代道家哲学也有“贵无论”,主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章),“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圣人藏乎是。”(《庄子·庚桑楚》)“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何晏:《道论》)由此看来,虚无主义本身根本就不是什么可怕之事,也不一定就“不对”。人类完全可以有一种世界观、一种“形而上学”是以无为本的。甚至可以说,欧洲虚无主义之所以可怕,正是因为它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而是有存在(或“存在主义”)作为其隐蔽的前提的,如尼采的虚无主义[48]。
因此,当海德格尔直接来讨论如何才能克服欧洲虚无主义时,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不在他的视野中,这就是:“为什么要克服虚无主义?”或者说,虚无主义又怎么啦?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即“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49]并不是一个事实问题,也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西方人可以选择“在者在”,而中国人则完全可以选择“无不在”(“无无”),因而这也是一个文化差异问题。海氏其实也是立足于文化价值立场而选择了“在者在”,不过他只是偶尔才流露出内心对欧洲虚无主义的价值崩溃的担忧或焦虑。如他说:“作为被掩蔽的和极端的存在之急需,无急需状态恰恰在存在者之晦蔽化的时代里流行,在人类文化的纷乱、暴力、绝望的时代里,在意愿错乱和昏聩无能的时代里流行。无边的痛苦和无度的悲哀既公开又隐蔽地表明:世界状况普遍地乃是一种充满急需的状况。”[50]
尼采的“古典虚无主义”的作用就在于揭示了人类的这种“存在之急需”状态,而“存在之急需依据于以下事实:存在乃是双重强制者,但在其悬缺中伴随着人之本质被消灭掉的危险,因为存在引发了对它本身之悬缺的忽略。”[51]很明显,为什么要克服虚无主义,以及为什么要思存在这个问题,最终所依据的是人的本质面临被消灭的危险这一事实,这正是一个价值事实。我们从这里可以发现,海氏不小心暴露了两种他自己曾极力反对的倾向,一是使存在者整体立足于价值之上,一是人类学和人道主义的倾向。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按照道家哲学的眼光,人的本质被消灭并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大不了使人归之于“自然”罢了;不但不必担忧,而且还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天人合一、人合于天的境界。一切纷乱、暴力、痛苦和悲哀都不必放在心上,可以当作自然现象来看待,做到“哀乐不能入”,这才叫做“真人”。至于意愿错乱和昏聩无能,那不过是思虑过多的结果,海氏想通过存在之“思”来走出这一困境,岂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可以设想,面临道家哲学的这一诘难,海德格尔必将方寸大乱。他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是他的价值选择和人本立场:我们是人,而不是植物或者石头什么的,我们当然不会愿意成为非人。这样,问题就会退回到尼采(强力意志)那里去,甚至退回到汉姆莱特那里去:to be or not to be,this is a question.存在还是虚无,这是个问题。这不仅不是个事实问题,甚至也不单是个价值问题,而是个文化问题。当海德格尔采用“欧洲虚无主义”(以及“西方形而上学”)这一表述的时候,他似乎是有一种文化自我意识的;但是当他设计克服欧洲虚无主义的方案时,他完全没有文化视野。
他没有意识到,地(“大地”)上本没有“路”,也不会无端地“涌现”(φυσι)出路来,所谓通向存在、通向语言、通向“思”之路是人自己走出来的,并不是放弃一切努力、无知无欲无为的结果,而是拼着“求意志的意志”来追求的轨迹。就此而言,他也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超出黑格尔和尼采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换言之,凡是他说得出来的,都最终归属于主体性的形而上学,而他超出(或自以为超出)主体形而上学的那种“意谓”(Meinungen),他却没法说出来;他的一切试图说出来的话语,到头来都不是超出了、而是更加强了主体性的形而上学。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海德格尔自己极力声称他是反主体性的、反形而上学的、反“人道主义”和反“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us)的,但人们都把他作了恰好相反的解读的缘故[52]。
人们是根据一个哲学家说出来的“话”来理解和评价他的哲学的,而不是、也不可能通过他没有说出来的内心意谓来理解和评价他的哲学。当然,如果他是一个诗人,或者像庄子那样,是一个寓言家,那又另当别论。但海德格尔恰好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爱智慧者”,是对智慧的话语、“逻各斯”的追寻者;他并不满足于用诗来说话,而是热中于用话来解诗,而用话来解诗,诗已经不再是诗了。
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困境,即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文化困境。他最为清醒地看穿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本质,即由尼采表现出来的那种“求意志的意志”的虚无主义;但他试图超出这一本质的努力就像试图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最终归于无效。这就是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所揭示的“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53]。至于欧洲虚无主义的克服,则不能依靠转向东方哲学(在东方哲学中虚无主义并不是什么困境),而只有通过西方自身的方式,也就是通过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来扬弃。主体性的形而上学不把存在者和存在本身割裂开来,而是力图通过存在者去追求存在,走上一条“自由之路”[54]。
在这条路上,目的性、合理性和辩证法、技术和艺术,都是缺少不了的载体,它们共同推进着现实的历史,并在这个历史中向人们呈现出越来越真切的价值目标——人的自由。历史主义是克服欧洲虚无主义的钥匙。
注释
[1]《尼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83页;又参看《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228-229页。
[2][3][4][5][7][8][10][11][12][13][14][15][16][17][21][22][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53][54]《尼采》,第734页,第671页,第910页,第912页,第757页,第756页,第705页,第1011页,第1016页,第995页,第680页,第431页,第969页,第831页,第718页,第735页,第739页,第994页,第693页,第965页,第970页,第966页,第967页, 第169页,第248页,第688页,第749页,第983页,第984页,第985-986页,第986页,第987页,第1025页,第1027页。
[6]所以尼采“可以把整个基督教理解为民众的柏拉图主义(两个世界学说)”,见《尼采》,第720页。
[9]例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有人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一种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却只是自己本身的反映,于是他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自身的假象,寻找非人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452页。
[18][20]《林中路》,第240、241页,第263页。
[19]这种轮回与加缪《西绪福斯神话》中对苦工的单调的承担还不尽相同,而是更接近于艺术家的独创精神。“对尼采来说,意志之可能性的创造乃是艺术的本质。”(《林中路》第246页)
[23]黑格尔早就指出过这一点:“力这一概念只有在它自己的现实性[或外在化]本身中才保持其自身作为本质,那作为现实的力只纯全在于表现中,而力的表现不是别的,只是自身的扬弃。”(《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5页)海德格尔的说法只不过重复了黑格尔的思想“:作为强力意志,存在者似乎先于并且高于一切存在而起支配作用。……这种现实之物摆出存在之物的样子,因为它同时自以为是那种决断的尺度,可以用来决定:只有起作用的东西——可感触的东西和印象,被体验的东西和表达,功用和成功——才应当被视为存在者。”(《尼采》,第1008页)“‘价值’本质上是功用价值”(《尼采》,第742页,又参看第335页)。
[40][41]《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48页,第151页。
[42]在场(‘存在’)作为在场常常是人之本质的在场,只要在场总是呼唤人之本质的指令。……如果我们试图透彻地想像‘存在’,想像它如何支配命运,即将它想像为在场,想像我们通过什么途径才能符合它的命运本质,那么‘存在’也就不再存在了。”见《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629页。
[43][44][45]参见《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631页,第662页,第697页——康德也可以说,撇开现象而思自在之物并不意味着两者的关系就不重要了,而只是意味着不要从认识论上来思自在之物,而在实践论上,却完全可以把自在之物(如自由意志)思作现象的“原因”或根源。
[46]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303-304页。孙周兴先生译Ereigenis为“大道”、“居有”、“本有”等;我主张译作“成己”。
[47]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92-194页;《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71页。
[48]正因为如此,与一些人猜测的不同,海氏对老子的欣赏是极其有限的。他欣赏的只是老子在存在者背后揭示其虚无本质的那种睿智,但决不会欣赏其对虚无主义的自得其乐的态度。
[49]《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页。
[52]就连海氏自己,有时也不否认这一点,如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承认自己所思的是“最充分的意义之下的‘人道主义’”,他为此的辩解是“:在这种人道主义中,不是人,而是人的历史本质在其出自存在的真理的出身中在演这场戏”(参看《海德格尔选集》第386页)“;人不是存在者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者”(同上,第385页)。但这种辩解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马克思的“历史规律”如出一辙,仍然属于主体性的形而上学的一种。
[53]参看拙文:《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对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的批评的批评》,收入个人论文集:《中西文化视野中真善美的哲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3页以下。
[54]海氏也看出:形而上学的本质“首先为存在的历史性的思想的经验允诺了进入自由之境的通道,而存在本身的真理就是作为这个自由之境而成其本质的”;同时“,存在本质性地现身,是因为它——即自由之境本身的自由——把一切存在者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本身,而且它始终是对思想来说有待思的东西。”(《尼采》,第1031页)当然,如何看待人的自由,在这里仍然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