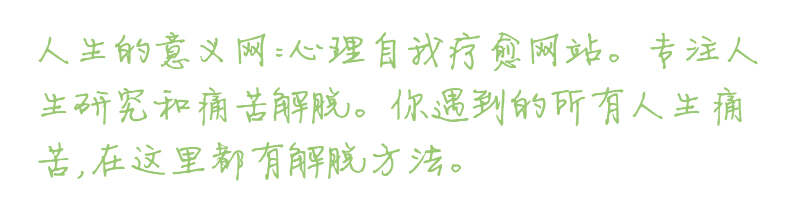癌症疼痛怎么办?一场本可避免的生死折磨

老朱又疼了,「死去活来」那种。
人瘦脱了相,萎靡在病床上,像被疼痛摄去了魂魄。头发和上半身都被汗水打湿,枕套已经能拧出水来。儿子小朱在床边陪着,又一次被无力感缠住。
这是老朱确诊肝癌晚期的第 208 天。
老朱今年 54 岁,现在的他,害怕天黑,因为癌症带来的疼痛,总在夜晚剧烈又尖锐地爆发。
疼痛是癌症患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国内每年新发癌症病例数超过 350 万,每四个初诊患者中就有一个发生疼痛。
癌症晚期患者中,疼痛发生率则高达 60% 至 80%。其中每三个患者中就有一个达到重度疼痛。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癌症疼痛诊疗规范(2018年版)》,疼痛级别量化表以 0 到 10 分的设计,重度疼痛分数为 7 到 10。癌痛是慢性疼痛里级别最高的一类。引起癌痛的主要原因包括三种:肿瘤直接相关、抗癌治疗引起、以及焦虑、抑郁等社会心理类非肿瘤因素。
乳腺癌患者刘荣说,2017 年肿瘤发生骨转移后,锁骨和肩膀的疼痛使她几乎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整日躺在床上,稍一动,疼痛便爆发出来。
刘荣给当时自己遭遇的疼痛的打分就是 10。
「那种疼,可比生孩子遭罪多了。生孩子是阵痛,疼疼就过去了,癌痛是 24 小时地疼,每天都疼,生不如死。」刘荣说。
在完全没有止痛治疗的情况下,刘荣捱了半年,肿瘤扩散,她反而不疼了。「现在回想,那时候要是知道止痛药有用,我指定吃药。能不痛就不痛。但那时不知道。」
之前,她曾服用过止痛药,但一周未见效果,医生建议加量,被刘荣以止痛药无用为由拒绝了。
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主任樊碧发认为,癌痛会让患者寝食难安,最终摧毁抗癌治疗的基础——患者的身体与精神。
「特别恶性的癌症,比如说胰腺癌,一般预期生存时间是半年到一年。但如果疼痛不控制,半天都过不去,患者就得痛不欲生,活不下去了。」樊碧发是国内疼痛学科的重要推动者和见证者之一。
在国内,国家层面不断呼吁和强调,癌症患者应该在医生的帮助下,科学、积极地处理疼痛。其中,药物治疗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方法就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三阶梯止痛法。
根据患者疼痛程度,医生可选用的镇痛药物的作用强度也会呈阶梯式由弱到强。第一阶梯为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和对乙酰氨基酚,比如布洛芬、阿司匹林;第二阶梯为弱阿片类药物,比如曲马多、可待因;第三阶段为强阿片类药物,如吗啡、羟考酮。
让患者免于疼痛是患者的基本权利已经成为国内外共识。因为对疼痛进行有效控制,不仅可以提高癌症患者的预后表现,更重要是改善患者生命质量,在生命尽头,维护为人的尊严。
现实情况却是,国内癌症患者仍然在普遍忍受疼痛折磨。
痛不欲生
被肝癌折磨的老朱,遭遇的疼痛有许多种。
先是肝部,随着肿瘤转移到胸壁,长出包块,疼痛也跟着咬住胸口,再往后,疼痛蔓延开来,人躺在床上,只要换个姿势就浑身都疼。
儿子小朱只能描述其中一种,「像小刀在摩擦骨头」。
老朱习惯忍痛。但疼痛还是逐步撕碎了他的忍耐极限和意志。
5 月中旬以前,老朱服用曲马多就能控制疼痛。按照「三阶梯止痛法」,曲马多属于二级阶梯药物。但 5 月下旬起,这种药物就在老朱身上失去了作用。
直到 6 月 7 日那天,他只告诉小朱,今天又比昨天痛一点。但转天,老朱就痛得掉泪了。儿子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记录父亲的病情。从 1 号发视频开始,主题就除了「痛」还是「痛」。
17 日的凌晨,止痛药不再管用,老朱仍旧硬挺着,不接受可以快速起效的止痛针。「今天打了,明天呢,怎么熬?」到了早上 5 点,人已经疼得直喊「妈」了。
21 号父亲节那天,老朱一直忍到凌晨 3 点 40 ,实在受不了了,把儿子叫醒,让医生注射了一支吗啡。
这一天,疼痛反复侵袭,每一分钟都似乎被无限地拉长。
夺走人的睡眠和食欲以后,癌痛把人耗得筋疲力尽。老朱难得能入睡时,小朱能听到父亲的鼾声。这种时候他忍不住感叹,「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相比疼痛在老朱体内的蔓延,对疼痛的控制似乎总是滞后一步。除了老朱自己忍疼以外,当地三甲医院的医生,也没能有效帮他止痛。
儿子小朱遵照当地医生的医嘱为父亲换上了属于第三级强效阿片类止痛药美硫酸吗啡控释片。但到 8 月上旬,老朱的疼痛已经发展到每 12 小时 270 mg 剂量,都难以控制的程度。跟初次用药量相比,已经翻了 9 倍。
目前用到 270 mg 的用量,也是由小朱做出的。他记得很清楚,父亲的药物加到每 12 小时 90 mg 时,管床大夫就提醒他「小心上瘾」。那还是 7 月 3 日的事。但他无法听从管床医生的建议,因为眼前的父亲太疼了。
为父亲做止痛决策的每一天,小朱都感到「如履薄冰」。
药量用多了,怕将本就脆弱的父亲推入人生的意义网的深渊,老朱吃止痛药会便秘、呕吐,这是肉眼可见的药物副作用。药量用少了,又没有效果。
一位看到小朱拍的视频,并与他结识的疼痛科医生告诉他:「止痛药的用量是没有极值的。」每当止痛药失去作用时,他可以按照前一天 1.5 倍的药量继续给父亲用药。但剂量到 270 mg 时,即便父亲已经痛到意识模糊,小朱也不敢再继续加量了。
小朱感到恐惧,他不清楚再加大剂量,会对父亲产生怎样的影响。
疼痛可控
事实上,大多数患者的癌痛问题可以得到完全控制。
不同疼痛科医生都告诉「偶尔治愈」,80% 到 90% 的癌痛可以通过目前的「三阶梯止痛方法」,降低到 3 分以下。这意味着疼痛被有效控制,对患者的睡眠、食欲、心情和精神不再产生显著影响。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癌症疼痛诊疗规范(2018 年版)》,对于慢性癌痛治疗,阿片类药物是中、重度癌痛治疗的首选药物。
像疼痛本身是主观感受因此存在巨大差异一样,阿片类药物在个体身上的效果也不同。癌痛诊疗规范中对于药物类型的选择、剂量的确定以及不良反应的控制都有明确的建议。
对于常见的对于阿片类药物的便秘等不良反应,在给药初期,应该注意并配合使用通便类药物等提前干预。而对于呼吸抑制等严重不良反应,通过逐渐加量、给药期间密切监视、使用催醒药物等手段也可以有效预防。
个体化给药是癌痛诊疗里,药物治疗的基本原则之一。疼痛作为一种主观感受,虽然有 0~10 级的量化评价标准,但没有客观的理化标准,个体差异巨大。
止痛药用量的确没有极值。中国解放军第七医学中心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刘慧龙对此深有感触。
他曾接诊过一位晚期胰腺癌患者,身体非常瘦小,刘慧龙只用了最低剂量的吗啡,那位老太太就熟睡了接近 12 个小时。而他治疗过的某位患者,吗啡的最高剂量为 1000 多毫克,但其疼痛依然没能完全控制。
「如果病人所有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疼痛没有得到有效控,就不应该说患者剂量差不多了,不能再增加剂量了。」刘慧龙说,「止痛技术含量、药物的拿捏难度其实并不大,主要还是(患者和医生)愿不愿意用,理念能不能放开。」
癌痛规范化诊疗的标准流程,其实包括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步骤,并非吃止痛药那么简单。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姑息治疗科)副主任医师顾筱莉表示,规范的癌痛诊疗需要对患者的疼痛作出正确专业的评估,其中包括患者既往的疼痛情况、药物使用情况、目前的疼痛评分,以及与所患疾病相关的情况等。量化、动态、全面的评估是癌痛规范化治疗的根本。
评估完成后,会参照三阶梯止痛原则等确定止痛给予的初始药物和初始剂量,进行进一步的药物剂量滴定,然后确定最合适的剂量。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重新评估疼痛,确定药物疗效,判断副作用等。其中可能涉及疗效不佳,剂量调整,增加辅助用药等,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临床过程。」顾筱莉说。
在执行癌痛诊疗规范好的医院,可以做到「333」原则,即在 3 天内,将癌痛等级降低到 3 分以内,每天的爆发性疼痛次数降低到 3 次以内。而在走得靠前的医院,已经能够做到「321」,即在 1 天内,将癌痛等级降低到 3 分以内,每天的爆发性疼痛次数降低到 2 次。
「止痛药的用量是按照癌痛诊疗规范内的要求一样。但这需要,比如说药物品种、给药方法、认知理念、对病人的观察等更进步和更精细才能达到。」樊碧发说。
然而,原本 3 天甚至 1 天就能有效控制的癌痛,现在仍长期折磨着大量的国内癌症患者。
止痛无门
理念先进,现实落后。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路桂军这样总结国内癌痛控制的现状。
国内疼痛学科的发展已经基本实现与国际先进理念的对接。樊碧发表示, 2016 年世界疼痛学科大会上第一次设立中国专场,用以介绍国内疼痛学科的发展成果和建设经验。
2019 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慢性疼痛对策事业政策研究班考察组到中日医院访问,目的就是交流了解中国疼痛学科发展现状和疼痛诊疗技术等内容。「90 年代,我是去日本学习疼痛的,过去 10 年中反过来了,他们向中国学习。」
这种转变得益于自 2007 年以来,疼痛科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从获批可以单独成立科室到疼痛科医生列入职称评级,再到成为国家重点建设学科,国家层面的力推让疼痛管理和治疗的理念在国内得到从无到有的质变。
但只有在止痛理念受到重视的医院里,癌症患者的疼痛问题才能得到规范化处理。即使止痛意识在肿瘤科医生乃至患者和家属中逐步普及,大量的患者仍然止痛无门。
「如果癌痛诊疗在国内更加规范的话,就不会有黑龙江的病人疼了三个月,到北京很多大医院看也看不好,最后碰运气来到我这儿。但凡有一个环节,比如说基层的二级医院能规范止痛,他也不至于疼到这来。」一位北京三甲医院疼痛科主任,同时也是疼痛学科内的知名专家说。
一方面原因,来自医生缺乏重视,且用药经验不足。
国内仍然有大量的医生对三阶梯止痛法不明就里,甚至是三级医院的一些医生也同样如此。普遍观点认为,疼痛只是疾病的一部分。因为长了肿瘤才产生疼痛,所有的注意力几乎都放在了生了病的脏器上。
然而,除了中晚期癌症患者群体普遍高发之外,抗癌治疗期间也会发生癌痛。据刘慧龙介绍,广义癌痛其实包括抗癌治疗带来的疼痛,很多都在早中期。
比如,一些早期患者手术后会发生神经痛;放疗患者局部皮肤或者脏器的疼痛普遍存在;而使用紫杉醇类药物进行化疗的患者中,局部静脉炎、骨骼和肌肉关节疼痛十分普遍。
另外一方面则是,患者和医生对止痛药成瘾根深蒂固的误解与恐惧——止痛药,尤其是阿片类止痛药所带来的成瘾担忧。
这种担忧让许多中国癌症患者活在疼痛折磨之中。也成为癌痛治疗在中国面临的最常见障碍。
刘慧龙说:「鸦片战争给国人造成的历史记忆太过惨痛。我 90 年代末参加工作,到现在也 20 多年了,相当一部分患者,也包括非止痛专业的医生,一听说阿片类药物,内心还有抵触。」
成瘾风险和担忧是目前使用阿片类止痛药最需直面的问题。
樊碧发说:「成瘾性是阿片的一个属性,一定要正视它。任何药物只要是药,它就固有毒性副作用,不可能全部把它避开。但针对癌痛,只要规范应用,成瘾概率很低,前提是规范。」
成瘾机制一般是当药物浓度在人体内出现连续波峰时,患者容易出现欣快感(即情绪出现病态高涨的状况),反复几次之后就会产生依赖,最终引起成瘾。
针对这一风险,止痛治疗强调规范、合理和科学用药。国内癌痛诊疗规范对于阿片类止痛药的用量设置了起始剂量,关于确定用量和停止用药,均强调采用渐进式的方法。
国内治疗癌痛的阿片类止痛药中,一般都是口服缓释剂型。一方面,可以让患者体内保持一定的药物浓度,控制疼痛,另一方面,则避免出现明显的波峰波谷情况出现。此外,患者按时按量服药也同样重要。
除了认为阿片类止痛药本身容易成瘾外,长期使用也会让人上瘾是另外一个担忧。
然而,疼痛得到有效控制后,经过医生评估,止痛药可以逐渐减量直至完全停用。伴随着癌症治疗进程,疼痛可能会减轻,此时止痛药也会慢慢减量直到停药。
此外,国内对于精神和麻醉类药物的管理,对于预防阿片类止痛药的滥用和成瘾问题,具有强力的控制作用。
「国内和国外有本质区别,国外一个处方可以开三个月的量,国内是 15 天,国外的阿片的药物不是癌症的也用,国内只有癌症才用,它有本质区别。国外的滥用是因为管得太松,中国则不然。」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路桂军说。
疼痛之外
为预防「药品」变「毒品」,各国针对麻醉药物和精神药物均采取特殊的管制措施。国内对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同样实行列管,并且要求在医院内有具备资质的专人负责相应药品的处方管理。
在国内,阿片类止痛药几乎都在列管目录中。国家卫生主管部门颁布的《处方管理办法》规定,对于需要长期使用麻醉或精神药品的中重度慢性癌痛患者,处方量为三天或七天。据了解,在一些医院癌痛患者的处方量被放宽至 15 天。
然而,虽然政策对于中重度癌痛患者有所照顾,但很多医院在实践中往往「一刀切」,对于管制清单上的止痛药往往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也更加敏感。癌痛患者成为付出代价的一方。
「怎么把握这条线,能控制得好,肿瘤病人都能用上药,还没有滥用的问题,这个当中有一个地带,确实很难。所以有的地方,就是宁可严一点,不出问题。但是严一点,对肿瘤病人的治疗就会带来一些问题。」北京一位三甲医院肿瘤科主任表示。
医院和医生都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以确保安全和控制风险。在医患关系敏感的当下,「很多基层医院都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造成在很多医院,要么所需的止痛药没有配齐,要么医生不愿意给患者用。
刘慧龙表示:「(因为非常严格),(药物)滥用的可能性倒不大,反而是医生慎用、用量不足的情况很普遍。所以我们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呼吁的,并不是注意不要滥用和避免不必要的使用,而是正常合理地使用。」
国内癌痛治疗参差不齐的背后,还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
一位北京三甲医院疼痛科主任表示,止痛需求最迫切的中晚期癌症患者往往最难得到有效救治,原因在于,国内缺少充足的临终关怀病房,肿瘤科室常常人满为患。
「医疗资源有限,患者想切割肿瘤都可能住不进医院,因为癌痛住院,谁会收你?」因此,即使很多大医院掌握癌痛诊疗的技术,也不愿意接收主要诉求是止痛的癌症患者。「(相当于)跟其他癌症患者抢医疗资源去了。」
同时,手术或者化疗等能为医院科室创收的手段,基本都不再适用这类病人,他们能为医生和医院带来的经济收益十分有限。「各科都有盈利压力在,没有什么盈利的病人,很少有人愿意承担。」
曾经风行一时的癌痛规范病房试点,现在在各地偃旗息鼓,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在这位疼痛科主任看来,解决中晚期癌症患者的疼痛问题,理想的状态应该是,饱受疼痛折磨的癌症患者能够在基层医疗机构得到规范治疗。患者在自己的社区,就能够接受规范的癌痛治疗,开到癌痛诊疗规范中的止痛药,而且负责照顾的家属也能够关注和重视到患者的疼痛问题。
当然,现实与理想状态依然有不小的差距。
老朱正在疼痛中缓慢滑向生命的尽头,他所在的医院还是当地的三甲级别,这是国内众多正在被癌痛折磨的患者群体的一个缩影。
癌痛带给他们更多痛苦,让家庭备受折磨,尽管规范和有效的止痛手段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