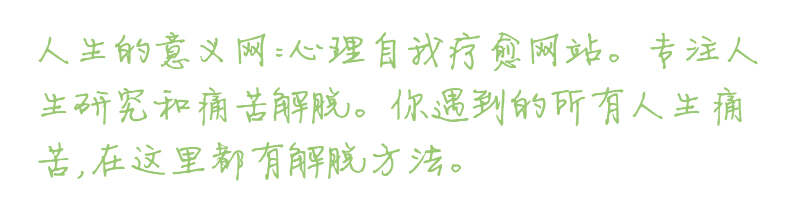萨特:“他人就是地狱”
2016-10-09 16:40:44 发布:人生的意义网

萨特认为现代人不仅感到孤寂烦恼,焦虑自欺,而且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也感受到压抑。由于萨特认为意识在其与存在的关系中,只能以“自为”和“为他”这双重模式而存在,因此研究与他人的关系便成“存在”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他的作品《他人》便成了萨特反省思考的结果。
一、“墨杜莎的目光”
在萨特看来,人与他人的关系有两面性,一方面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来说,他人是我们身上最为重要的因素。“他人是我和我本身之间必不可少的媒介……我需要他人,以充分完全把握我的存在的所有结构,自为回归于他人……”另一方面,他人与我的关系通过注释而呈现为互为主奴的关系,在他人的注视下,我的自由消失了,变成了物一样的自在的存在,变成了为他的存在和对抗,变成了非我的客体”,“我被他人占有;他人的注视对我赤裸裸的身体进行加工,它使我的身体诞生、它雕琢我的身体、把我的身体制造为如其所是的东西,并且把它看做我将永远看不见的东西”,他人掌握了一个秘密:我所是的东西的秘密。他使我存在,并且正是因此占有了我,并且这种占有不是别的,只是意识到占有了我。”我仿佛像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在过路行人的注视下,变成了与公园花草长凳树木一样的只有定不变属性的物,成了他的占有物或奴隶。可是另一方面,我也是具有自由意识的自为的存在,在我的注视下,他人也同样变成自在的存在,变成了我视线内的物,成为客体,成为我的奴隶,这样一种人与他人的关系便是互相为主奴的关系,这样一种注释的眼光便是“墨杜莎的目光”。
墨杜莎是古希腊的一个神话人物,她是众怪之父福尔库与刻托所生的一个女妖,据说她本来长得十分的美丽动人,由于她试图与美神雅典娜比美,结果被雅典娜变成了一个最丑恶的妖怪:她长着双翅利爪和夹齿,头发是许多缠绕在一起的毒蛇,她的面目狰狞可怕,两眼闪闪发光,谁要是见了她的目光,谁就要立即变成石头。在萨特看来,墨杜莎的光会使人变成石头,而他人的目光则使我变成物,“他人出现之际,把一个在世界之中的自在的存在’作为事物中之一物赋予臼为。这种由于他人的目光而产生的自在的僵化乃是墨杜莎神话的深刻意义之所在。”因为在“注视”中,每个人都尽力保持自己的主体性,而把他人当做客体。“一方面我要设法从他人的掌握之中解放我自己,另一方面他人也在力图从我的掌握之中解放他自己;一方面我竭力要去奴役他人,另一方面他人则又竭力要奴役我。这样他人的存在造就了人世间的冲突和纷争,冲突是为他的存在的原初的意义。
二、“他人就是地狱”
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一哲学思想,萨特通过独幕剧《禁闭》形象地表现了“他人就是地狱”的情景。《禁闭》描写的是三个幽灵在象征着永恒的地狱的旧式客厅里的活动。一个是由于背叛祖国而被枪毙的加尔森:一个是因赶走丈夫的情妇致使丈夫自杀而被判罪的同性恋者伊内斯:一个是溺死自己亲生的私生子而犯法的艾丝黛尔,这三个鬼魂互相角逐、互相折磨、互相纠缠,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时,就有第三者进行破坏,他们谁也不能脱离别人的牵扯而自由地行动,谁都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谁都不得安宁,永无休止地钩心斗角,使他们陷入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最后主人公加尔森终于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地狱原本是这样,我从来没有想到……提起地狱,你们便会想到硫磺、火刑、烤架……啊!真是天大的笑话,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狱。”
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此语一出,惊世骇俗,遭到许多人的批评与误解,一些人指责萨特过分悲观地夸大了人与人间关系的否定方面。对此,萨特一方面坦率地承认,“如果我总是把存在主义的某些面貌悲剧化,那是因为我忘不了在集中营中经历过的感情;那时,我经常地、赤裸裸地在别人的目光中生活,而地狱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另一方面,萨特又竭力为自己辩解:‘“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总是被误解,人们以为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刻都是坏透了的,而且永远是难以沟通的关系。然而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本意,我要说的是,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被破坏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
可见,萨特认为他人就是地狱不是指正常的人际关系,而是指变质的被扭曲的异化的人际关系,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一种病态的人际关系在哲学思想中的反应。萨特深刻地指出造成这一异化关系的原因在于人完全丧失了自由和主动性,完全依赖于他人,依赖于他人对自己的判断。萨特特地说明《禁闭》中主人公故意用三个幽灵,意在提醒大家,他们并不代表存在的真正关系,只体现了一种变异的相遇,说明我们与他人的现实的关系并非不存在其他可能。当然,萨特用“死人”也是有所指的,具有象征性,意在指出“有许多人被禁锢在一系列陈规之中不能自拔,他们对自己抱有他们本人也为之痛苦的看法,然而他们却没有设法加以改变。……如果谁总是在为他并不设法去改变的看法和行为而烦恼不安,那么谁就是一个活死人”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他人才是地狱。
显然,这里萨特的思想和他“人就是自由,人不外乎是自己造就的东西”的思想一脉相承,遥相呼应。他从人的存在与自由出发,从人的选择与责任入手,反对任何人主宰自己的自由,反对摒弃自己的意愿,用外在的束缚限制自己,从而将自尊和价值全部建立在外在的评判和标准上,致使自己一直生活在“失去自我”的他人的目光中。萨特在追忆他的童年时,坦率地承认自己曾一度也是这样,竭力在他人的眼光下扮演一个好孩子的角色,“我学会了用他们的眼光,即使是大人不在场,我也感觉到他们投射来的目光,我就在这种目光下奔跑嬉闹,这目光给我们规定了模范幼辈的圈子,不敢越雷池一步,决定着我的游戏和我的天地”,儿童纯洁的天性,活泼的童趣就这样在外在的束缚下逐渐失去了。萨特认为,如果人一直这样的话,他们的自由就逐渐丧失,生命力渐渐萎缩,以致蜕变成活着的“死人”。
萨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由于我们都是活人.所以我想以荒谬的构思来揭示我们自由的重要性,也就是通过其他行动事改变我们为之痛苦的行动的重要性。不管我们处于何种地域般的环境之中,我想我们都有自由去打碎它。如果有谁不去打碎它,那就是他们自由地留在其中了,也就是说,他们自由地将自己置于地域之中。”这样的人也是无药可救的,只不过是活着的失去自由与灵魂的行尸走肉而已。
三、积极的行动与荒谬的人生
为了唤醒更多活着的“死人”,为了自由不被窒息,萨特提出“人的惟一希望是在他的行动内,行动是使人活下去的惟一事情”的行动哲学。以萨特之见,自由是与人的存在共生,因此,无论面对多么束缚而扼杀人的自由选择的境遇,人都不应该举手投降,麻木不仁,消极被动,而是要行动。行动才是自由的表现,只有行动,才能显示人的自由,才能显示自己的意愿与价值,才能昭示人的存在。“人实现自己有多少,他就有多少的存在,因此,他就只是他的行动的总体,他就只是他的生活。”如果你拥有卓越的写作才华,那么用你的艺术作品区表现吧;如果你是运筹帷幄的将军,那么战场则是你发挥才能的地方;如果你拥有无限的爱,那么去在爱的过程中体现爱吧。总之,不要将这些停留在口头、想象、梦幻中,除此之外,惟一要做的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人无非是自己行动的总和”。
萨特强调“不冒险,无所得”,强调行动的重要。“存在的人是把自己的存在孤注一掷,碰碰运气的人”,然而萨特的人生哲学最终没有摆脱存在主义人生哲学的悲观的阴影。他感叹道:存在是没有原因的,没有必然性的,存在的规定性本身就向我们表明了它固有的偶然性,人就生活在偶然中,一个人的整个生活经历就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人生莫测,一切选择和行动都是偶然的无目的的,生活同样也是无目的,无意义的。正如萨特作品《作呕》主人公洛根丁所言:“在生活中,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只不过是背景经常变换,有人上场,有人下场,如此而已,在生活中无所谓开始,日子毫无意义地积累起来,这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单调的增加。”
不仅如此,这单调的日子也是荒谬的。萨特认为,“荒缪,这不是我脑子里的一个观念,也不是一个声音,而是我脚下的这种没有生命的长蛇,这条木蛇。不管这是蛇,或者是爪子或者树根,或者秃隐,都没有关系。虽然没有清楚地阐明什么,我却是懂得我找到了‘存在’的关系,我厌恶的关键,我生命的关键。事实上,我紧接着能够理解的一切,都可以归纳到这种根本的荒谬里去。”更为可怕的是荒谬的日子注定走向死亡,人生也是一场必然要输的赌博。“我的整整一生都留在我的后边。我完完整整地看到它,我看到它的形状和一直把我带到这儿的缓慢动作,对它没有什么好处的,只不过是我赌输了,如此而己。三年前……我输了第一回,我想赌赢第二回,我又输了,我全盘输了。这一下我就懂得人总是输的,只有混蛋才相信自己会赢。”所以,人无论付诸什么行动,最终人总是输的。
人的一生无论如何冒险、获取,最终却都是以死亡为结局。因此萨特得出了人永远不能超越不幸意识,因为这是他的本性,“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的悲观主义结论,至此,萨特的人生哲学在自由的帷幕下宏伟地拉开,却在虚无与死亡中惨淡地落幕,颇有一番从“数风流人物看今朝”的凄凉与悲哀。
纵观萨特的自由、选择与责任的人生哲学,我们不难发现他最大的特点是矛盾性。萨特的思想乐观与悲观,希望与绝望为一炉,这既是萨特所处的风云变幻的时代的真实反映,也是他那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内心的生动写照。正是因为萨特人生哲学思想的矛盾性,所以它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以“自由观”为核心的人生哲学揭露了西方社会对自由的压抑,号召人们从安之若素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自己设计、自己选择、自己行动、自己造就自己的思想,无异给那些西方社会中急于忘却往事、摆脱现实、寻求出路的知识分子指点迷津。但另一方面,由于他没有从根本上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因此他的绝对自由、绝对选择、绝对行动,往往也是主观愿望而已,它并没有把人从压抑中摆脱出来,反而又让人带上了沉重的责任和镣铐,品尝了孤寂、烦恼、焦虑与自欺,易于走入个人主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歧途,这可以从萨特的人生哲学俘虏了西方当时的“嬉皮土”、“愤怒的青年”、“垮掉的一代”和“现代的崩克”中窥见一斑,它其实是西方社会部分知识分子急于摆脱又苦于找不到出路的真实写照和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