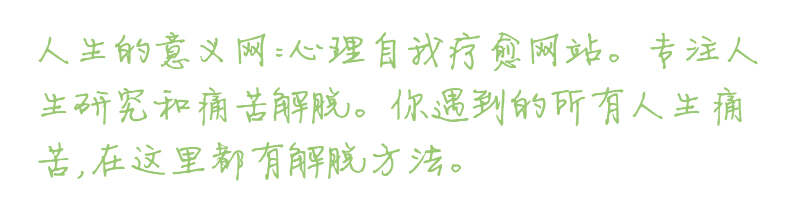萨特:自由、选择与责任
2016-10-09 16:40:52 发布:人生的意义网

如果说“存在先于本质”、“人不外乎是白己造就的东西”是萨特人生哲学大厦的基石的话,那么“自由观”则是支撑萨特体系的擎天立柱。他以此为支架,论述了自由与存在、自由与选择、自由与行动、自由与处境、自由与责任、自由与烦恼等等关系,全面架构了他的存在主义的人学大厦。
一、自由与存在
萨特认为,既然“存在先于本质”“人不外乎是自己造就的东西,那么使人从空泛的纯粹的存在、露面到生命的展开过程,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造就、规定自己的就是人得自由。
它和人的存在相伴相随。只要人一出生,在人生的舞台上一露面出场,自由就在人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一动一静、思考与行动中,展示它特有的力景与魅力,它不是一个人可有可无的属性,也不在乎你是否承认接受它,更不是从人之外强加于人的东西。相反,只要你是人,只要你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享有自由。自由是存在的不可分割的孪生体,自由早就人的本质。“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悬置在人的自由之中。因此我们称为自由的东西是不可能区别于‘人的实在’之存在的。人并不是首先存在以便后来成为自由的,人的存在和他‘是自由的’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简言之,存在就是自由,没有自由也就不可能存在,自由与存在之间不是二者选一的问题,而是不可选择的问题,它是与生俱来、命中注定与存在相伴相随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特发出了“人是被判自由这种徒刑”的感叹。“我命定是自由的,这意味着,除了自由本身以外,人们不可能在我的自由中找到别的限制,或者可以说,我们没有停止我们自由的自由。”
自由就是存在的宣言,是萨特心目中关于人的学说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人摆脱了中世纪匍匐于上帝的脚下拱手出让自由的奴性与谦卑;又揭开了文艺复兴时期人虽自由,但自由却是上帝赋予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羞答答的面纱;更打碎了近代黑格尔等把自由当成人的本质,但却置身于理性名义下的桎梏。至此,自由既不依附于上帝,也不从属于理性;既没有任何规定性,也不是人的本质。自由只是存在的同义词,自由是人不可抗拒的命运,自由与人的存在生死与共,休戚相关。自由与人同在。
二、自由与选择
在萨特看来,这种自由是一种自主选择的自由,是人按着自己的意愿自己选择自己、创造自己、规定自己且最终造就自己的自由。因为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人一出生只是纯粹空泛的存在,它犹如一张白纸,需要在自由这支笔的操纵下,通过不停地涂抹行动,绘就人的本质的图画,必须通过自由的选择使自己塑造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由此,萨特认为自由就是选择,而选择的主体是单独的个人,因而选择是个人的选择,它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一句话,自由就是个人的自我选择的自由,这种选择的自由造就出个性独特的本质,演绎出五彩缤纷的人生。
这种选择是无条件的,由于存在与自由合二为一,而自由又意味着选择,故人不能不选择。即使决定不选择,这还是一种选择,所以选择和自由是一样,都是人不可抗拒的命运,人只有无条件地接受。
这种绝对的选择,它在人的思想或意识的王国里,没有任何牵制与羁绊,惟有想像与自由相伴随。这是一个萨特心目中的自由的王国,它与常识的自由王国泾渭分明。常识的自由是指获得满足而达到目的的能力,而萨特的自由意指选择目的的自主,至于目的达到与否却是无关紧要的,即“明确地说明‘是自由的’这种表达不意味着‘获得人们所要求的东西’,而是由自己决定去要求。换言之,对自由来讲,成功与否是无关紧要的。”萨特以关押在监狱中的俘虏为例加以说明,如果说身陷囹圄的俘虏仍然是自由的话,萨特不是指有随时越狱的自由,而是意指他有随时企图越狱的自由,前者是常识的自由,后者是萨特所言的自由。
前者注重的是能力和获得,后者注重的是愿望与选择,所以萨特谆谆告诫人们必须注重获得的自由与选择的自由两者的本质区别,不要以能力的不自由否定愿望的自由,萨特的自由只是思想选择的自由。
三、自由与境遇
真实的人生面对的是现实的世界,从想像王国进入到现实的天地,自由便遇到它的障碍与阻力——境遇。一方面,我命定是自由,这意味着除自由本身以外,人们不可能在我的自由中找到别的限制;另一方面,我只是现实的我,只能在一定处境中生活,处境与自由就构成现实的矛盾。萨特对此采用自由的悖论来化解这一矛盾,即一方面处境并不是单方面对自由的限制,因为处境通过自由才得以显现;另一方面,真实的自由总不能一味拘泥于思想的王国,它也只有在处境中才能得到反应,才具意义。
客观两言,萨特承认境遇是自由展现的舞台,这一舞台不容置疑地给自由设置各种各样的限制与束缚。他曾经说过:“人不过是一种境遇,人完全为其阶级、收入劳动性质所制约,甚至人的情感和思想也受这些条件制约。”这是萨特自由思想的客观性表述的闪光之处,而且萨特的自由的悖论中,“自由既是对处境的否定性脱离又介入处境的,自由只有从一个给定的处境出发并通过对这种处境的虚无化的逃离才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即在处境中方凸显自由的思想,无疑也是其辩证的思想。然而更多的时候,萨特强调的重点不在于此,而是认为自由作为人的存在的同一性,不可能在境遇的压迫下就丧失了选择的绝对自由的特性:就是在森严壁垒的集中营,在阴冷恐怖的监狱,在严刑拷打的威逼下,人仍享有自由,享有选择反抗与屈服、逃跑或认同、招供或缄默等的绝对自由,这样一来,萨特将自由的一只脚跨进境遇的门槛之时,又偷偷摸摸将自由的另一只脚缩回到内心意识的空间。不仅如此,萨特为了固守绝对自由的天地,在自由与境遇二者的关系上,有意凸显自由的主动性,反对境遇的被动性,他认为境遇不是对自由的否定和取消,而是对自由的确证和显明,任何境遇要想成为障碍,也必须在自由的介入下,才有意义,否则它只是与自由无关的境遇而已。
萨特以人生的几种境遇为例对此予以说明:首先,就人的产生而言,人的确是被抛入世界而处于某一位置上,置身于一个并非自己自愿选择的环境中,但这个位置的意义是人自由选择的。举例来说,同处于贫穷的家庭,贫穷对一些人来说是发奋的动力,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也可能是偷窃的内因,也就是说,一个贫穷的家庭这种不可选择的境遇仍然没有限制人的选择、行动的自由,相反却是自由赋予境遇意义。
其次,人的生命是一条由过去、现在到未来相连接的路,过去能以过去的境遇限制现在的人的选择的自由吗?萨特认为过去并不能制约现在,过去对现在的意义也是由自由赋予的,过去的历史可能让现在的人骄傲,也可能是现在的人的负担,骄傲与负担是自由赋予其过去的意义。
再次,工具性的事物作为境遇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也是取决于人的自由选择:“一块岩石,如果我想搬动它,它便表现为一种深深的抵抗,然而,当我想爬到它上面去观赏风景时,它就反过来成为一种宝贵的援助。……它是中性的,也就是说,它等待着被一个目的照亮,以便表露自己是一个对手还是一个助手。”
最后,死亡作为人无法逃避的境遇是否能够限制自由呢?死亡是人终不可逃避的命运和结局,死亡的阴影总是威胁着活着的人,有的人一想到死亡的结局的无可逃避性,就整日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死亡对这些人而言则变成了致命的限制。古代哲学家伊壁鸠鲁曾说过: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并没有来临;而当死亡来临时,我们并不存在,为什么要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呢?萨特的思想与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萨特认为死亡不能限制自由,因为限制别的东西的终将是自身确定的东西,而死亡却是自身不确定的,死亡把一切存在变成曾存在,因此死亡不是在存在之内,而是在它之外的东西。人的自由活动本身并不受死亡的限制,它正像人的出生一样,是一种绝对偶然、荒谬不可理解的东西,死亡的意义是自由的生命的给予的,因此死亡是以自由作为前提而存在的,它对存在或自由都不会成为限制。
萨特从这些方面力图固守他的选择绝对自由的思想堡垒。这有两个原因:其一,萨特认为自由是一种意识的状态,这是理解萨特自由观的关键。“大体说自由正是这种意识的状态本身,它表现的方式不依赖任何东西。它不由先前的时刻决定——也许与过去时刻有关,但这种相关完仝是自由的,从一开始起,我就把这种意识看成自由……我正是由于一种意识状态的性质而总是感到自由。正是自由和意识是同一个东西,理解自由和是自由是同一回事,所以萨特认为一个人在任何环境中,任何情况下都是自由的。其二.强调绝对自由的意义是为了给在德国纳粹统治下不仅物质上极其艰难,而且精神上极其压抑的法国人民以自信和勇气。一方面医治法国人的后悔病,要人民保持尊严,另一方面要唤起法国人民呼吁他们为自己的自由起来抵抗。萨特通过其文学作品《苍蝇》表达了其写作的用意就在于“在《苍蝇》中我想谈自由,我的绝对自由.我作为一个人的自由,首先是被占领的法国人对德国人的自由。”
四、自由与责任
萨特认为既然自由是绝对的选择的自由,那么“命定是自由的人”必须肩负着选择自己的命运、造就自己本质的重担和责任。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它是存在与自由选择的必然产物,任何他人和社会都无法为你承担自己造就自己的绝对自由选择后果的应负的责任。正是因为自由的选择,自由的行动造就自己的本质、自己的人生,那么他理所当然得为自己负责,这是强调选择的绝对自由的萨特要演绎推断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和目的所在。“如果说存在确实是先于自己的本质,人就要对他的本性负责,存在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并且对自己的存在负责。”
个人不仅要对自己的选择承担所有的责任,而且还必须对人类全体对世界负责,“如果存在先于本质,如果我们存在的同时也创造了我们的形象,那么这形象就对所有的人,对我们整个时代都有作用,这样一来我们的责任要比我们想像的大得多,因为它关系到人类全体。”萨特对此进一步加以说明“假如我是一个工人,我可以选择成为一个基督教工会会员,不参加共产党的工会,由于这种选择,我是在表示,人生在世最好是清静无为,人的天国不在世上,我就不是为我选择这种观点,而是为所有的人选择了清静无为。”“再举一个更属私人的例子,我决定结婚生子,即使这一决定只是根据我的情况、情欲和愿望做出的,但这实现了一夫一妻制,就涉及到整个人类。”由此萨特得出结论:“我在对自己负责时,也对其他所有人负责,我在创造一种我自己想要的形象,我在创造自己时也创造他人。”
显然,萨特赋予人的责任太大了。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仅关联自己、关联他人甚至关联整个人类,现实如此沉重,责任如此重大,作为选择主体的孤零零单个的个体是如何承担起这一责任?在行动中有无任何可供依据的价值标准作为行动的指南呢?
尼采曾经:“人是价值的判断者和创造者”,萨特颔首赞同他认为作为统一价值的上帝早已随着上帝死了的呐喊而消逝,那么一切价值都相对于人自己,造就自己本质的自由就变成了衡量一切行为价值的惟一尺度,“自由是人的规定性,是最高的价值”。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标准,那种以过去的经验为根据,以现存的道德规范、习惯作为外在根据和道德权威的价值判断只是人逃避自己的责任、逃避自己选择所负后果的一个借口而已。在萨特心目中,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任何行动,任何选择,只要出自你的愿望,出自你的选择,而且你能承担起由此而来所负的责任,那么无论你决定什么都是允许的和道德的。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书中引用了一个故事来说明其观点,大意是他有一个学生,其哥哥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牺牲了,为了给哥哥报仇,他想去参加自由法国军队,可是家里中有一孤单痛苦的老母亲需要他照顾,由于分身无术,他面临着两难选择,是去参加法国的军队呢?还是留下来陪伴母亲?如果参军就要抛弃母亲,于心不忍;而留下来就不能给哥哥报仇,此恨难消。留下来是安全的,出路也是具体直接的;但是如果去参军,就可能出路未卜,艰险重重,甚至因为牺牲和其他理由而半途而废。此时此刻,这位青年举棋不定,犹豫彷徨,求助于萨特。
萨特认为在这种两难选择中,既没有任何客观规范和道德原则告诉他怎么做,也不能听从教师、神父和任何导师的权威,因为任何别人都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提出各种劝告,不可信赖的,所以萨特的答复是:“你是自由的,所以你选择吧”,原因在于“没有普遍的道德标准能指点你应当怎样做:世界上没有任何天降的标志。”这样无论如何决定,只要是你自己选择的,就都是允许的道德的,萨特把是否道德的评判标准完全归于是否出自人的自由选择上,道德标准的客观性、社会性、历史性消失殆尽,使他从绝对自由选择出发滑向了道德评价的虚无主义。
在萨特的心目中,“所谓价值,也就是你所挑选的意义”。自由选择既无根据,又无确定的标准,因而任何选择都可以发生,都是偶然的,因而也都是可能是具有相同意义的,“我意识到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只不过是瞬息即逝的,价值并不是事物和行动本身所具有的,而是我所赋予事物和行动的,只要我们的选择是出自内心,是自由的,那么选择就具有正确性。”任何决定只要是“处于自己心里的选择,就是它们在内容上,代表着完全相反的道德,他们的价值也是等同的。”
在萨特那里,一方面人被判自由这种徒刑,由此戴上了沉重的责任的枷锁;但另一方面他又借道德价值评判无标准性、虚无性,暗度陈仓,把对他人、社会沉重的责任感悄悄地瓦解,形同虚设,以便让负荷之下的个人舒缓一下压力,但由于个体的自由选择造就自己本质,个体的行动是要承担个体命运的责任,所以个人自然无法避免地活在烦恼、焦虑和自欺中。
五、自由与孤寂、焦虑和自欺
自由选择的人吞下的第一枚苦果便是孤寂。这是因为:一方面,人是自由的,你可以自由选择、自由地行动,可以不断地告别过去走向未来,并在一系列的选择和行动中展现能力,证明存在的价值,造就自己的本质:但另一方面,没有上帝和规定的道德规范,没有任何普遍的价值标准,你自己承担起在自由的名义下为自己选择的责任,自己为自己立法,在生活的道路上,没有人替你出谋划策,没有人指引你应该往哪条道路的哪个方向走。这样在茫茫宇宙中,在芸芸众生里,你会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孤寂感从心底里油然升起,仿佛自己是行进在仿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行的道路上,只有孤寂如影子般紧紧相随。
自由选择的人吞下的第二枚苦果便是焦虑或烦恼。萨特认为正是因为你感到孤寂;感到无人可依无法可据,一切靠自由选择,一切祸福自己扛到肩上,这样大的压力与责任独自默默承受,你在选择时难免陷入烦恼或焦虑之中。所谓的烦恼就是指我们在进行自我选择时有无法避免掉的全面而深切的责任感,“任何人如果专心致志于自己,并且明白不仅是他自己所挑选的人,而且也是同时挑选人类和自身的立法者,那么,人就无法避免掉他的全面的和深切的责任感,因此人生下来就带有烦恼。”就会陷入一种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烦恼之中,一种冥思苦想不得其法的烦恼之中,一种不敢轻举妄动又不得不动的烦恼之中,烦恼是自由选择、自由行动、自己负责必然的伴随物。
存在主义者克尔恺郭尔也讲人生的孤寂与烦恼,不过他是从上帝的存在出发的。因为人在上帝面前是罪人,他随时都有一种罪孽感,这是人无法摆脱的情绪,因此他感到孤寂和绝望,这种孤寂,烦恼,畏惧,绝望便成为人的存在方式,构成了他生存的基本经验。弗洛姆是从人与自然的分离、个体化的角度入手,个体化一方面赋予人自由,但另一方面又让人感到孤独、乏力、软弱不安,尤其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异化更是把这两方面的矛盾推到极致,所以他得出“现代人你的名字叫孤独”的结论。萨特与前两者均不同,他是从上帝死了,存在存在于本质,人不外乎是自己造就的东西入手,推出人的绝对自由与责任、孤寂与烦恼。虽然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却殊途同归,把孤寂和烦恼当成人生不得不吞咽的苦果。
如果人注定是自由的话,那么人同样是注定焦虑的。焦虑是人对世界的本体论体验。他认为“正是在焦虑中人获得了对他的自由的意识,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还可以说焦虑是自由这存在着的意识的存在方式,正是在焦虑中自由在其存在里对自身提出问题。”焦虑是不可消除的,因为“我们就是焦虑”。但现实世界的人们往往是想尽方法逃避焦虑,这便是“自欺”。“自欺”是一种自我辩解的态度,“这种态度本质上是属于人的实在的,而同时又像意识一样不是把它的否定引向外部,而是把它转向自身。这态度在我们看来就应该是自欺。”所以“自欺”不同于说谎,说谎是意识用谎言对他人隐藏了事实真相,说谎是二元的,说谎者本人明白事情的真相,却又用谎言掩盖它。而“自欺”则是意识对自己掩盖事实真相,是在单一意识的统一体内部发生的并不涉及自身之外的他人,这里无所谓欺骗者和被欺骗者,或者说两者都是同一个人。如果说说谎是意识把否定引向外部的话,自欺则是把否定转向自身,是自我表现否定。换句话说,人在现实世界上总是否定他自己原本的样子,而使自己符合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这就是自欺。或者说,人的存在与他现实在世界上的存在并不是同一的,前者是自由选择的,后者却不是自由选择,而是被迫扮演出来的。萨特以一位咖啡馆的侍者为例来说明:“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咖啡馆的侍者。他有灵活的和过分的、过分准确,过分敏捷的姿态,他以过分灵活的步子来到顾客身边,他过分殷勤地鞠躬,他的嗓音,他的眼睛表示出对顾客的要求过分关心,最后,他返回来,他试图在他的行动中模仿只会被认作是某种自动机的准确严格,……他的整个行为对我们似乎都是一种游戏。他专心地把他的种种动作连接得如同是互相制约着的机械,他的手势,他的嗓音都似乎是机械的;他显示出了一种物的无情的敏捷和速度。他表演,他自娱。但是那时他演什么呢?无需很长时间的观察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扮演的是咖啡馆的侍者。”
萨特认为,这个咖啡馆的侍者并不像“这墨水瓶是墨水瓶,这玻璃杯是玻璃杯那样干脆就是咖啡馆侍者,”他可以有其他选择,“按他所思的方式是他”。但他根据他人的意愿自愿扮成咖啡馆的侍者,机械地做出与侍者身份相符的标准动作,他试图实现的,是咖啡馆侍者的自在的存在,这样他本人的存在和他作为咖啡馆侍者的存在并不是同一的,他以不是其所是的方式实现着自欺。
在萨特的思想中,自欺有时表现为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自在的存在,即是与物一样的存在,或者表现为人把自己仅仅看成是别人要他成为的那种人,即把自己当做他人的一个客体而存在,也就是充当一个为他的存在,所以自欺在意识和他生存的真实状况之间竖起屏障。虽然有时通过自欺可以逃避焦虑,但却牺牲“自为的”“存在”为代价,与自由作为人的选择行动上最高准则相背离,所以萨特谴责自欺,他借文艺作品《恶心》、《一个工厂主的童年》、《波德莱尔》对种种自欺人给予了有力的鞭挞。
无疑萨特看到了西方社会人的存在的一种病态现象。海德格尔曾说,人走向世界,就是自欺自弃,人是被抛入物的世界。由于人无法摆脱周围社会和他人而生活,同时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必然要受到社会和他人的干扰和限制,因此产生忧虑烦恼和恐惧。现实的人对此就企图把自己的真实存在融化到他人的存在方式中,融化“众人”中,从而想别人所想,做别人所做,去过无个性的生活,因此海德格尔发出了“社会是沉沦了的人的祖国”的感叹。
弗洛姆也指出现代人为了摆脱自己日益增加的自由意志及由此日益增加的孤独软弱不安,便采取一种“从众”的方式,放弃个人的自由权利,与众人保持一致,顺从众人的意志,服从群体的观念信条,遵循社会的风俗习惯,致使“工作程序化,娱乐公式化,生活标准化,”变成没有个性,没有特征的千人一面的大众人,由此而来可以看出“自欺”、“从众”固然是和萨特的“自由”相悖,但却是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即使社会常常迫使人“自欺”,那么人与他人的关系又是怎样呢?萨特的回答是:“他人就是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