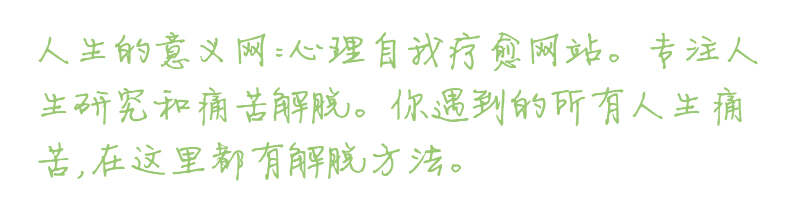《庄子》人生论探析
2016-10-09 16:46:07 发布:人生的意义网

自《庄子》一书诞生之日起,人们对它的接受和阐释就由于切入角度的不同而显得异彩纷呈:或从哲学角度,以佛解庄,以玄解庄,以儒解庄;或从审美心理、审美享受、审美判断等方面来应和《庄子》中的某些章节。从创作的主观动机来说,《庄子》多多少少带有探索哲学、美学问题的意识;但如果结合庄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征伐杀戮、人命危浅——的现实来讲,笔者认为庄子更多地是在谈论人生。
《汉书·艺文志》载《庄子》有52篇,至郭象注庄则又成了33篇,到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庄子》,这期间版本的变更比较混乱复杂,《庄子》一书的原貌我们只能推测,因此今天看《庄子》经常会产生关于种种矛盾的疑问。上世纪80年代,张恒寿《庄子新探》和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等为代表,比较充分地论证了内七篇为同一思想体系的作品,而外、杂篇则有庄子后学所作。本文接受这一文献考证前提,以内篇为主,兼取外杂,来探讨一下《庄子》的人生论。
一、立足现实,思考人生困惑
庄子生活的时代是战国,天下为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所分割,弱肉强食,实力强的诸侯国通过外交、战争等各种手段对弱小的诸侯国进行蚕食鲸吞,小范围的掳掠、大规模的征战此起彼伏。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刀光剑影,交融着血与泪的混乱时代,人的处境是异常险恶的。上有喜怒无常之暴君,如:
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人间世》)
下有勾心斗角之群小,如: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知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热,姚佚启态。(《齐物论》)
处在这样一种现实之中,人们是整日凄凄惶惶,充满了忧生之嗟的。庄子立足于此,展开了对现实中的人生问题和人生形而上层面的思考。
在《逍遥游》和《齐物论》中,庄子是由物论及人生的。《逍遥游》篇之旨意传统上有两种经典解释,即郭象的大鹏与小鸟都逍遥和支道林的大鹏与小鸟都不逍遥这两种结论。笔者认为,庄子在这里并不重在讲二者究竟谁逍遥的问题,而是在讲物性之差异,由此引出逍遥的话题。《逍遥游》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风之积也”厚才能“负大翼”。而蜩与学鸠则是“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之二虫”以己之性来揣度大鹏,而二者的物性是存在差异的,故而它们会发出“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的嘲讽,所以它们并不逍遥。《齐物论》也注意到了物性的差异:“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以此物之物性来度彼物、对待彼物,或者会不逍遥,或者会伤彼物之性。人言有别,故物论有分。于是就有了是非之争,有了困此而进行的杀戮、纷争,有了口诛笔伐、流血漂橹,于是天下“嚣嚣也”(《骈拇》)、“哼哼矣”(《肱箧》)、“匈匈焉”(《在宥》)。但这种争论果真有意义吗?果真能有结果吗?因此由此引起的争端在庄子看来也是很荒唐的,他在《则阳》里就借一则寓言给予了尖锐的嘲讽:“戴晋人日:‘有所谓蜗者,君知之乎?’日:‘然。’‘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日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日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其次,庄子阐述了生死问题。一个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固然是新的希望,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从诞生那一刻起,又已经一步步向死亡走近了。人生命的倏焉而来、忽然而去的偶然性和短暂性是人类无可奈何的悲哀,尤其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中,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另外,在人的一生中,不可能一帆风顺,挫折和不幸或许会时时袭来。如何对待人生中的忧苦,如何对待人类短暂一生的终点——死亡,也是庄子思考的人生问题之一。
再次,庄子思考了人生的意义,即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而庄子却完全打破了其神圣性,俨然以一副蔑弃政治的姿态将战国时代那些有雄才大略的霸主所津津乐道的最大的式功——治天下抨击得一文不值。庄子在探讨人生意义的时候较多以政治设喻,这也是符合当时社会背景的一种言说方式,较易为人接受。如果一个人有用,介入社会,实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那么或许就会伤生,如他所举的比干、伍子胥、介子推等人的例子。但如果无用、与世隔绝或者虚与委蛇,那岂不成了一种“行尸走肉主义”《人间世》“匠石之齐……见栎社树”与“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两段以及《山木》篇中关于材、不材的论辩都涉及到了这一问题。而相对于前面所提到的纷争、生死,庄子在这一问题上则显得尤其矛盾,甚至无奈地以诡辩等语言游戏来自我解脱。
二、徜徉大道,消解人生悲苦
陈鼓应在《庄子的悲剧意识和自由精神》中论道:“庄子则属于阿波罗式的精神境界。庄子的悲剧意识……激情也被恬静所取代,……他的逍遥游并不是出世的,而是寄沉痛于悠闲之中。”庄子立足于现实思考人生问题,然而现实的残酷性却使他无法在这片土壤上进行积极的人生价值体系的构建,而仅仅是创造出许多人类思维难以认知和体会的极其抽象的概念和境界,来对人生悲苦进行消极的、阿波罗式的静观的消解。
人世间的争斗源于有是非、善恶、正邪等对立的观念,如同物性存在差别一样,人类的观念也是有差异的,庄子是清醒地认识到并正视这一现实的。要彻底消除人世的纷争,达到和谐,就必须取消上述对立,就像《德充符》中所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因此庄子提出齐物论,并发明了一系列性质相似的概念以消泯上述对立,如“以明”“道枢”“环中”“天钧”“两行”“天府”“葆光”“心斋”“坐忘”等等,通过这些让人看来匪夷所思的方法来达到一种原始的、虚无的、混沌一片的状态。《齐物论》玄“齐”并非整齐、齐一,因为物性、物论本身都是有差异的,不可能抹杀个体性的差异,所以,笔者认为“齐”应该解释为既保存物物之间、物论与物论之间的差异性,同时又不产生对立性。这样,就不会在《齐物论》“大智闲闲”一段所描述的尔虞我诈、互相罗织构陷的险恶人际关系中受到伤害。另外,庄子还为我们描述了一种人类意识和思维体验难以达到的超人间的境界、状态。《大宗师》对其有大篇幅的描写,其他篇章也间有涉及,如《应帝王》:“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在宥》:“出入六合,游乎九州。”天下、外物、生死都不能使之受到伤害,人世的纷争又怎能打动他那颗宁静超然的心呢?他们是真正逍遥的。
庄子认为“死生,命也”(《大宗师》),对生死持一种安处的心态,不以赋形为喜,亦不以死亡为悲。《齐物论》:“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另外,庄子还创造了“物化”(《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气”等概念并用它们来解释人生中的忧苦和死亡问题。如<养生主》:“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日:‘……适来,夫子时电;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这样一来,人生的忧苦就不再那么令人感伤,它们只是造物的安排,人们只需安常处顺、顺其自然即可。生死也不再那么令人欢欣或是悲哀了,它们只不过是一物到另一物的转化,是气的聚散而已。庄子用这些概念彻底消解了人类生命之慨的永恒悲哀。
对于人生的意义,在《齐物论》中庄子就发出了疑惑和感慨:“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蔚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人生在世,是有用好还是无用好呢?是介入社会争名逐利还是介然独立虚与委蛇呢?对此,庄子显露出了极大的矛盾。看下面几则材料:
惠子谓庄子日:“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日:“……令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遥游》)
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而问于蘧伯玉。日:“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人间世》)
庄子看到了个体与社会的矛盾、无用而保全自身与有用而伤生之间的矛盾。那么人是坚持原则介入社会还是仅仅为了保全生命而无知无虑地成为行尸走肉呢?表面看来,庄子是认同上面所举的无用之用的例子的,但事实上庄子极认真,极讲原则,单看《秋水》中“惠子相梁”“庄子钓于濮水”两段和《列絮寇》中他尖刻地讥讽曹商就可对他这种品质窥豹一斑。庄子这种人“最具崇高感……对人性的美和尊严有一种内在的敏感,心意坚定沉着,真诚正直……他有一种温厚而高贵的情感。他的忧郁并不是因为失去了生活的欢乐,而是因为他的感情强烈到超出一般的限度……他的感情和行为都是以最高原则,即普遍的善良意志为根据的。他的言行举止不受别人的判断的影响,只依靠自己的独立见解。他不为变幻不定的表面现象所动摇,一旦抱定宗冒,便义无返顾……这种人富于思想……讨厌卑贱的奉承,胸中充满自由精神”[胡。他痛恨世间的种种丑恶,痛心生灵涂炭的现实,无用之用、材与不材之间以及像《人间世》所讲的“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只是他迫于现实想出的看似可行而实际上绝对不可能而他也不甘心如此的无奈的自嘲、自保方式。从以上所举的例子来看,庄子是不愿由于介入社会而伤生的,但他又不愿意无原则地混世苟活,所以他站在宇宙的、终极的角度采取了对介入社会积极构建人生价值体系进行解构的方式来消解这种矛盾和悲哀。像至人、神人、真人那样抛弃物累,不“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在超人间的绝对自由中实现逍遥游。
三、结语
我们说庄子浪漫,然而这浪漫背后却是残酷的现实。庄子立足于现实难以找到消解人生悲苦的有效途径,而只能徜徉大道,创造出许多人类思维难以认知和体会的极其抽象的概念和境界来对人生悲苦进行消极的、阿波罗式静观的消解。
庄子是浪漫的,庄子又是最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