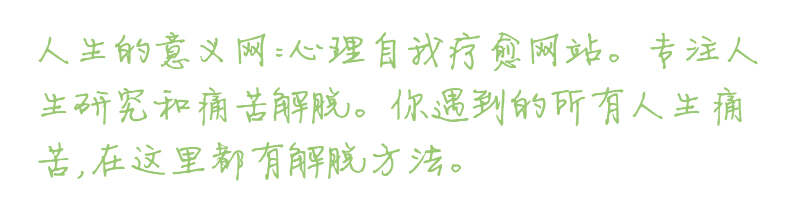一篇通俗、精彩的海德格尔存在主义解读:家是存在的语言
2019-11-25 14:17:23 发布:人生的意义网

家是存在的语言
在此大众文化风行、传播媒体当道、文化泡沫沸腾的信息时代,心浮气躁、肝火旺盛的中国学者对任何西方思想家的理解都是浅尝辄止,惟有海德格尔除外,没有哪位当代西方思想家曾象海德格尔这样在中国激起如此经久不衰的阅读热情,近年来,海德格尔的著作被接二连三地翻译出版,然而,这些书究竟有多少人能耐心地读完并心领神会,却实在不敢说。毕竟,海德格尔太令人费解了。
一、聆听存在的深度
海德格尔之所以显得费解,是因为他的语言完全不符合人们熟悉的哲学语言的路数,不仅是因为其文本中随时可遇的陌生的用语,更由于他的语法和修辞常常完全溢出语言常规,哲学语言应是环环相扣丝丝入缝的论证,沿着山重水复的逻辑路径曲径通幽,直达最终的结论,然而,海德格尔却似乎故意跟语法闹别扭,与逻辑过不去,他的话语中到处都是故弄玄虚的语言游戏、闪烁其词的修辞圈套,让读者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实际上,海德格尔确实是故意跟语法和逻辑过不去,并通过这种对语言的诗意运用消解常规语法和逻辑,最终颠覆语法和逻辑植根于其中的形而上学传统。
海德格尔的话语之所以费解,正是源于他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源远流长,在西方历史上曾以各种各样的变种出现,然而,无论形而上学如何变化,却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各种形态的形而上学总是不言而喻地将其话语策略设置于主体-客体二元论的基础上。形而上学(以及奠基于其上的科学和学术)是关于人及其世界的话语,也就是说,它总是要对什么东西有所言说,而任何事物一落言筌,一成为话题,不管它是石头、天体、人还是神,都立刻被转变成了现成的对象或客体,而谈论者则顺理成章地成了自我或主体。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以说是语言无可逃避的宿命,因为,我们总需要有面对一个如此这般摆在那里的东西才能言之有物,才能有话可说。我们只能在形而上学的话语格局中说话,或者说,人一旦想对什么有所言说,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形而上学的罗网。如果说形而上学是一个错误,那么,这个错误的根源深刻而久远,它几乎就是人类的命运,人类早已习惯了它以及它的语言方式,别的语言方式反而显得是费解的胡话或空洞的呓语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就被英国分析哲学家艾耶尔斥为毫无意义的昏话。
海德格尔竭力想摆脱并颠覆这种形而上学的话语格局。海德格尔哲学之思和诉说的话题是存在,但按他的理解,存在不是形而上学或传统的本体论所标榜的的实体,不是已经在什么地方在场的现成对象,人们只要对它进行一番由表及里、由粗到精、去伪存真的观察、分析,就能够把它之所是加以描述和表述,并进而作为真理或知识传达给别人。形象地说,存在不是在我们之外的或干脆被置于我们对面的什么东西,我们无法置身于存在之外,我们永远只能沉浸在存在之中,存在无所不在、无边无际,它支撑我们、庇护我们、供养我们、照料我们。我们只能在存在之中,对之进行体悟、领会,而无法置身其外,对之进行观察、描述。存在不是在我们之外的客观对象,我们无法对之打量观察一番然后对它进行谈论,存在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即之不在、无可言说,毋宁说,倒正是存在才展开并限制了我们的视界,才使我们能够看和说,存在是我们的视野和言语赖之而展开的东西,它决定着我们如何看、看到什么、如何说、说些什么……,存在不是我们能够如此这般对之观看一番谈论一番的摆在那里的对象,相反,存在是我们能够如此这般地观看和谈论的可能性前提,存在让世间万物栩栩然地呈现出来,澄明无遮,然而,存在在让存在者无遮呈现的时候,自身却隐而未现,违莫如深,存在者越醒目,存在越隐晦,这就是海德格尔喋喋不休地谈论的澄明与遮蔽之间的辩证法。
但海德格尔却要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其不可道,却偏要道之,其存在论就是要对此不可言说的存在进行言说,但是,不可言说的东西又如何能够言说呢?常规的话语策略显然是行不通了,必得发明一种新的话语方式。或许,存在虽然不能作为话语的“所指”被表述和描述,但由于语言本身就是植根于存在的,当我们执着地依恋着存在而有所道说之际,存在的神秘也就自然而然地随着道说而展现出来了。
这正是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的话语策略。
他不再象传统的本体论那样试图对存在是什么、存在怎么样──亦即对存在的本质和定性进行描述和界定,因为,存在不再是人们可以对之如此这般地进行观照然后对之说点什么的东西,或者是现成地但却隐隐地潜藏在某种帷幕(如现象或假想)背后有待于哲学家去发现并将之摆到明处让人承认的东西。人作为人,就已经在存在之中了,即,已经存在了,在人──包括哲学家──意识到并开始追问存在的问题之前,人就已经在存在中了,──这里的“之中”,却并不意味着存在是一个现成的空间或境界什么的,似乎我们可以自愿地进去或退出。──不如说,人,就已经是他的存在。存在不是兀立在我们对面让我们打量观照的对象,而是隐身在我们身后支撑着引导着启迪着我们观看的目光和言说的脉络,我们在存在中,而不是存在在我们之外。人存在,才能思考和言说,包括思考和言说存在的问题,或者说,人存在着而言说,说,本身就是一种存在的行为,因而,存在,也就在每一种言说进行之际而被道出了,被触及了,也因此被照亮了,虽然,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澄明可能是遮敝着的澄明,即存在在被掩盖着呈现出来。存在,并非是可以被语言从某个在语言之外的什么地方捕捉到并予以公布的“所指”物,话语总是存在的言说,话语是徜徉于存在之林的幽径或开放在存在的幽暗之域中的花朵,它并非指谓存在,它只是通向存在之域的暗示或“路标”,因此,不能言传,而只能意会,不可观照,但却可以体贴。
既然任何一种言说都可以道出存在,因而,对存在的思考和言说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而不必局限于由传统本体论所约定俗成的传统的话题,存在论并无什么专门性或优先性的话题。因而,海德格尔的哲学演讲和写作,给人留下的一个独特印象就是,他虽然也经常谈论一些为过去的哲学家津津乐道的非常玄妙的题目,如时间、空间、物、真理、科学、存在等等,毕竟,作为哲学的从业者,他不能拒绝哲学家们业已习惯了的共同语题,不能拒绝与传统和同行对话,但是,他更喜欢谈论的却是一些在正经哲学家看来不伦不类不着边际的因而不屑一顾的非哲学的话题,在正统哲学家看来,甚至想到这些问题,都是罪过,更不必说在哲学杂志上一本正经谈论它们或在哲学讲坛上海阔天空地宣讲它们了,海德格尔所津津乐道的话题或术语,如烦忙、出神、大地、澄明、裂缝、光、居住、桥梁、门槛、林中路、遮敝等等,都是哲学家闻所未闻的,是由海德格尔才第一次带入纯洁的哲学殿堂,在关于存在的大部头著作中,他可能长篇大论地讨论一把锤子或汽车方向标,在关于真理的演讲中又会对一双梵高笔下的破旧的鞋子大发感慨,诸如此类,海德格尔的哲学话语往往教人耳目一新或不知所措。
海德格尔哲学话语策略的特异之处不仅在于他可以随手抓过任何话题将听众引入存在的秘境,而且还在于他对这些话题的谈论方式,这里我们不可能对海德格尔的哲学修辞进行全面的分析,只举出一点足矣。按理或者按习惯,讨论哲学这样深奥的话题,其话头应该徐徐地道出,让读者或听众做好心理的铺垫,以便跟得上说话者的思路,而在讨论的当中,则应该摆事实、讲道理,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展开论证,最后得出明确的结论,以便令听众心中有底,放心而归。但海德格尔的哲学话头却常常无端而来、无端而止,说话当中又常常无端地横生枝节、左顾而言他,倒颇有点禅宗当头棒喝的机锋。
试看一例:
“……人诗意地栖居……”此诗句引自荷尔德林后期一首以独特方式流传下来的诗歌。诗的开头曰:“教堂的金属尖顶,在可爱的蓝色中闪烁……”倘我们要得体地倾听“……人诗意地栖居……”这个诗句,我们就必须审慎地将它回复到这首诗歌中。因此,我们要思量此诗句。
这是《“……人诗意地栖居……”》讲演的开头,而其结束则是用了荷尔德林而另一首诗《远景》。
再看一例,其题为《语言》的演讲是这样开始的:
“人说话。我们在清醒时说,我们在梦中说。我们总是在说。哪怕我们根本不吐一字,而只是倾听或者阅读,这是,我们也是在说。甚至我们既没有专心倾听也没有阅读,而只是做某项活动,或者悠然闲息,这当儿,我们也总是在说。
这次演讲同样是在一首诗的吟唱中结束的。
可以说,海德格尔开创了哲学话语和写作的新文体,而这在哲学史上的意义甚至比提出一种新的观点或问题来要重要,因为,一种新文体,一种新的话语方式,也就是一种新的运思方式,它在旧的哲学视野之外,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从而大大地拓展了哲学的疆域,赋于哲学以新的生机。当代哲学图景,正是从海德格尔开始才焕然一新的。
海德格尔摧毁了原来横亘于哲学与其他领域之间的话语壁垒,没有什么话题是哲学不能谈论的,然而,并非任何方式的谈论都能算是哲学的谈论,哲学谈论的目的是为了呈现存在的奥秘。因此,在谈论的过程中必须牢牢地“把握”存在,这里用“把握”一词实在是免为其难,因为,我们在存在中,存在并非是某种我们可以捕捉于掌或用眼睛紧紧盯住不放的什么东西,眼睛的视野总是有限的,被眼睛把握的东西不是存在,存在总落于视野之外。为了表达对存在的领会,海德格尔更愿意用“倾听”一词,倾听存在的声音或沉默,听是不受疆界或视野限制的,当人们屏息凝心、收视反听,纯朴的存在,就会象一片天籁,从四面八方悠悠而起,洋洋乎盈耳。
倾听,对海德格尔来说,可以发生于任何行为中,在任何行为中,人都可能与存在相遇或擦肩而过,而倾听就在这时发生了。当然,海德格尔并非在字面意义上使用“倾听”这个词,并非指用耳朵感官去听,而要用澄明无私的心灵去听,不仅用心灵,而且更要用活泼泼的肉体去听,去体会。倾听,就是要自我放逐的现代人,重归存在,在其中留恋逍遥、恬然栖居,重温存在那家园一般的温情和宁静,承受那源于历史宿命深处的谆谆叮咛。
西方思想关于人类认知和理解的思考,一直是立足于视觉或观看的隐喻,认识就是观看,主体就是一个观看者,世界就是由作为观看者的主体和被观看的客体所组成的,而形而上学或者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回答这种观看是如何可能的,主体的目光,如何能够穿越横亘于我和物之间的距离、透过纷繁陆离的表象看到事物内部的本质,弥合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裂缝,这一问题,是西方哲学自诞生之日其就挥之不去的困惑。实在说来,这一困惑是形而上学或认识论所注定无法克服的,因为形而上学或认识论原本就是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分裂生发出来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原本就以这一裂缝作为存在的基础,几乎所有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基本术语和基本命题,都基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观看隐喻,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就意味着彻底抛弃主、客体二元论的存在图式,意味着以这一存在图式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自我瓦解、自我废黜,同时也就意味着从根本上放弃视觉隐喻。
在海德格尔那里,观看就被倾听代替了,存在不再是被观看的对象,而一个被倾听的深度或虚廓。实际上,对于人类知解力而言,倾听是较之观看更源远流长的认知途径,在漫长的史前时代以及在广袤的日常生活中,人类主要不是依靠文字和图像,而是依靠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依靠风行大地、流传千古的歌谣、史诗、言传身教和口头传统来负载和传承知识的,因此,对于人类先民和世俗大众而言,吟唱的能力较之刻画的能力、倾听的能力较之观看的能力,更重要也更亲切,正是通过倾听,那些世代传诵的箴言、教诲和启示才穿越遗忘和时间的距离,把世世代代的人们和他的祖祖辈辈的祖先、神灵以及天籁流行的大地联系起来。只是随着历史轴心期的到来和知识阶层的诞生,随着城市和国家的产生,随着书写取代吟唱、文字取代口说,成为主要的知识载体,眼睛才取代耳朵,成为主要的认知器官,而观看也才取代倾听,成为主要的认知方式,人们才开始基于视觉模式构想、组织其知识的获取和传承方式,视觉隐喻因而成为思想和知识的不言而喻的出发点。倾听使人归属于声音,将人浸透于无边的声音之域,让人追随着声音的律动和感发而不知不觉地心驰神往、心醉神迷,把倾听者化为声音旋律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倾听让人忘我,使人皈依,来自存在的声音穿透倾听者的身心,与造物沆瀣一气,与万物磅礴为一。而观看则相反,观看意味着分裂和疏远,观看者只有拉开和对象的距离才能观看。倾听让人沉入存在幽暗的深渊,而观看则让人漂浮在事物光亮的表面,观看无法洞悉存在的深度和奥秘,深度只会让观看者头晕目眩。面对存在的深渊,观看者极其目力,也无法洞穿深渊的黑暗,而只会迷失于深渊上方光怪陆离的变相,相反,一滴自天而降的雨水,落入深渊激起的泠然余响和渺渺回音,就可能让倾听者测度出存在的深度和广度。
二、家是存在的尺度
人在存在中,人对于存在只能倾听而无法观看,人对存在的这种姿态恰如其对于家的姿态:人在家中,家庇护和包容着人,如同存在一样,家也不可能转换为对象,家只有有人居住时才算得上家,人也只有居住于家中才能体会和理解家的意义,一旦置身于家园之外,把家当成观照和描述的对象,家就不再是家了,而变成了所谓“民居”,变成了与雕塑、绘画等同类的供人观赏的造型艺术作品了。
在此,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把西方哲学史对存在的追寻与中国诗人们对家的渴望相对比。中国诗歌中一直回荡着对家的眷恋,如果说西方哲学的历史是丧失存在的人们追寻存在踪迹的历史,中国诗歌中则到处回荡着浪迹天涯飘泊江湖的无家可归者或有家难归者关于乡愁的诉说,也许只有陶渊明是一个例外,陶渊明与屈原、李白、杜甫等被放逐者或自我放逐者不同,他不是一个天涯行客,而是一个在家园中劳作的农夫,在诸多关于家园的讴歌中,惟有陶渊明能够道出家的安详、温暖、质朴和自在,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恰恰是因为他不是在乡愁的追忆中把家变为一个遥远的对象,而是在静守家园的岁月中体贴家园的风流蕴籍,并用朴素的洋溢着乡土气的语言道出家的真情实感,正是在这一点上,陶渊明才是无可比拟的。而陶渊明之所以能够与家园体贴无间,不过是由于他不像别的中国古代文人那样,虽然眷恋家乡但却舍不得功名利禄或一片经世济民的抱负,从而在不归的红尘路上越走越远,陶渊明毅然的舍弃尘网归田园居,“田园将芜,胡不归!”是对故作姿态的中国文人的当头棒呵。
与此类似,海德格尔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断然拒绝日益繁荣和霸道的现代科学和技术而回归源初素朴的存在,他不像大多数现代知识分子那样一方面义愤填膺地抱怨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的戕害,一方面又沉湎于由现代科学巩固得越来越僵化和顺畅的形而上学话语策略而无法自拔,海德格尔以截断众流的果敢断然拒绝嚣嚣不息的常规话头和流行话语,在他山上的小木屋中,在谦逊的沉默中,细心聆听诗人和风的歌唱。
正因为存在与家园之间这种可比性,海德格尔才形象地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对海德格尔来说,存在不再是语言可以随便谈论的对象,存在不再是存在于语言之外的客体,而语言只是可以指谓它的符号,语言就是存在,存在也就是语言,存在与语言浑然一体,存在只是因语言而在,语言也只是存在的言说,语言澄明了存在的疆域,而存在也敞开语言言说的可能性。语言与存在的这种关系,正如语言与家园的关系:家园并非人们可以观看的对象和称述的客体,毋宁说,倒正是家园,才展开了人们的视野、并引导着他对在视野中涌现之物的道说:我们凭藉那幽幽屋宇和深深庭院,了望深邃的碧落、广阔的大地,凭藉窗下花丛、墙头衰草倾听潇潇春雨、习习秋风,凭藉桑榆夕照、棂间星光领会时辰流逝、季节轮回,凭藉瓜棚闲谈、炉边夜话承受村落的历史和民族的宿命──离开了家,不仅我们的身体无所安顿,我们的视野也将无所凭藉,我们将不仅无法领会家,而且将无法理解世界,无法领会宇宙的辽阔和历史的久远。我们的祖先把世界命名为“宇宙”,就表明他们正是凭藉家园领会世界的:“宇”和“宙”,在古汉语中原本意谓房子的屋檐和栋梁,先人们凭借屋宇领会宇宙的深远和广阔,而宇宙,则是庇护我们身体、安顿我们心灵的屋宇。世界是围绕着家园展开的,家园就是人们所领受的最初的世界,人们的世界观是建立在家园之上的。离开了家园,离开了对由家园风物所设置的熟悉的路标和晷影的参照,迷失于无边的陌生之地,人们将失去度量自我和万物的尺度,人们将无法把握空间和时间,也就无法领略和道说世界。正因为只有凭借家园的话语,我们才能领会和言说存在、度量宇宙和万物,因此,海德格尔的箴言颠倒过来说也同样成立,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所以“家是存在的语言”。
在海德格尔哲学格局中,存在与家园之间有着无微不至的映照关系,把握了这种可比性,并从这种可比性出发去阅读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玄谈”,初读海德格尔时遭遇的困惑将涣然冰释。海德格尔的语言并不费解,也并不古怪,起码不比充满了抽象的术语和生造的概念的传统哲学话语费解。毋宁说,哲学语言只是到了海德格尔这里才真正地返朴归真了。他的语言并不玄虚,而毋宁说非常质朴和平易近人,因为,存在,对于他不再是超越的抽象的哲学或神学实体,而就是人们日日悠游其中而不知所之的平凡家园,它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身边,却又离我们很远,回避一切抽象的语言,他因而就只能用谈论家园的一往情深的感性语言谈论存在,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就是家的哲学。听它的哲学演讲,仿佛是在聆听一个老者在谆谆叮咛一个即将离家远游的少年,无论走到那里,都要把家乡记挂心间,而家乡随时都会亲切地接纳风尘归客。——说到底,一种关于家的哲学话语,必定是天涯游子早已熟悉却又早已生疏了的乡音,乡音是世界上最简单纯朴却最意味深长的语言,我们甚至常常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演讲中听到乡巴佬式的方言土语,这对于高度雅化了和虚化了的哲学语言来说,简直是空谷足音。
存在就是家,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就是家的哲学,他的哲学话语就是家常话,我们阅读海德格尔的哲学作品,有时却是如同在聆听一个见多识广的老者话家常,就如同聆听陶渊明在向我们数家珍似地念叨“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以及檐后的柳榆、堂前的桃李、巷中的狗吠和树上的鸡鸣。海德格尔后期的哲学演讲和写作中,越来越少见那些充斥着西方哲学著作的司空见惯的抽象术语,如自我、主体、客体、本体、实体……,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哲学话语逐渐地从玄妙、繁琐、纠结的传统哲学语境中解放出来,正如同陶渊明的诗,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然而,海德格尔的语言又总是意味深长的,并不因其朴素而浅薄、枯淡。我们把他的哲学话语比作拉家常,但家实际上是最难谈论的,因为家是人们每日每时日常起居之所,人们对家太熟悉,而家对人们也太平凡,平凡得几乎被人们忘却了,以至于人们只有在离开家时才能猛然醒悟,才能想到家,才能意识到家的可贵,家的一切也才能历历在目地呈现眼前,人们也才能情真意切地对家进行诉说。人们对自己每时每刻居于斯长于斯的自己的家,甚至还不如对邻人的家更熟悉。因此,家虽然是人们最熟悉谈论的最多的,但同时又是人们最陌生最难言说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之可贵正在此,他能够用最平淡最朴实的语言道出家园,说出不可说的东西,让家园的神秘、平凡和幽暗在其诗歌中自在呈现。海德格尔的卓越也正在此,他用哲学闻所未闻的平凡的语言道出了存在,道处了人们身在其中而不自知的存在家园,而且,存在,在海德格尔的笔下不再如同在那些哲学经典中那样抽象、玄虚和超越,可望而不可亲,而是重新变得诗意盎然、风流蕴籍,甚至一块石头,在海德格尔的笔下都获得了丰富的质感和生动的色相,而不再是一块沉浊的质料,深邃的碧落、丰沃的大地、多彩的世界、可敬的神灵、迷人的精灵,重新环绕在人们的周围,庇护我们的身体,慰藉我们的心灵,清风吹拂,河水流淌,万物灿烂开放。海德格尔的哲学话语是朴素的,但淡到极处也是浓到极处,海德格尔的哲学话语又是丰腴的、意味隽永的,海德格尔将哲学变成了诗,实际上,他的哲学演讲或写作常常就是围绕一首诗的独白,常常就是从诗开始又以诗结束,而哲学原本就是源于诗的,海德格尔使哲学重归其诗的源头。存在,人们关于存在的领悟,正是在诗歌中才初次呈现并藉诗歌而得到保存。
海德格尔的哲学演讲中引入了不少新的词语,但他并非是故作高深或玩弄辞藻,他用的实际上恰恰是词的字面意义或曰语文意义,而并非其哲理意义或玄学意义,只是这些语文意义往往被哲学的陈词滥调和日常的闲言碎语掩盖了,因此,海德格尔不得不常常求助于语源学、训诂学甚至方言学,以拂去沉积在语词真义上的尘埃。对他来说,对语词本真意蕴的揭示,同时也就是存在的澄明,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对语词源始意义的寻觅,因此同时也就是穿过幽暗的语言之林向存在家园的回归。
而人们──尤其是哲学教授和学徒们之所以听不懂他素朴的话语,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哲学行业的从业者,已经在哲学的行话中浸淫的太久,已经不习惯简单明白地说话,也听不懂简单明白的话语了,正如中国汉代的儒生已听不懂《国风》中那些野人天真的歌唱而一门心思地要从中看出后妃之德和王道教化一样。海德格尔不遗余力地凸现语词的字面意义,不是为了显示饱学,而是为了把哲学从其行业性的失语症中解救出来,让哲学学会人间话语,学会讲人话。
然而,他的这一努力究竟有多大成功的可能呢?他又如何避免自己的独语不被现代传媒的喧嚣所淹没、不被顽固的哲学积习所歪曲?实际上,海德格尔本人已清楚地预见到了这种危险,而我们从当下渐见兴盛的关于海德格尔的翻译、研究中,不是也已经明明白白地目睹这种危险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