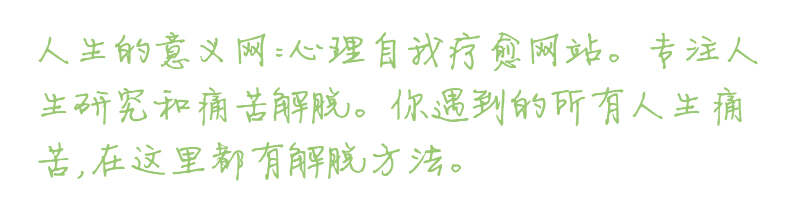行业|心理病也是时代病

心理病也是时代病
我从2000年左右开始从事正式的心理咨询工作,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一个明显的感受是:人们心理问题的层次越来越丰富,文化环境和时代的变迁在其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大多数来访者存在的问题都是神经症。简单地说,来访者的性格、人格发展都是完好的,心理上没有什么重大缺陷,在现实生活中他/她可能是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好老师好医生,社会适应良好,但他们的内心痛苦纠结,所以来寻求帮助。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痛苦是因为他们内心的一些本能需要和严苛的道德标准相冲突导致的。
如果以西方心理咨询的发展作为参照,我们会发现西方精神分析的产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两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宗教和神学的影响衰落。原本人生问题有《圣经》提供终极答案,但当这个答案被否定之后,人到哪里去寻找答案,如何去面对价值观的冲突?心理咨询成为了某种替代渠道。在弗洛伊德的著作里,他的个案大多数也是神经症水平的,他的理论同样适合于治疗神经症水平的来访者。弗洛伊德为什么提出性欲理论?正是因为那个时代,性是禁区。人性被压抑的这个部分导致了强迫症、癔症等心理障碍。
类似的情况其实也出现在中国。在过去三四十年时间里,我们也经历一个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多样化的时代。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早年,我接触过的很多来访者患有一种典型的神经症叫作“恐人症”。这种症状在西方很少见,多见于东亚文化。在日本,它被称作“赤面恐怖”。这类来访者在社交场合的时候不敢与人目光对视,一旦对视,脸唰地就红了。
脸红是羞怯的表现,基本上都跟性有关系。我国早期著名心理治疗家钟友彬对这种神经症提出过一套认识领悟疗法。他发现,来访者在进入了青春期以后对异性产生了欲望,但是他们的道德观念又告诉他们这种性的幻想是肮脏的。他们之所以不敢与人对视,是因为他们担心周围的人会看穿自己,自己会被视为流氓。道德观念过强,压抑了本我需求。而现在我们对待性的观念更加开放,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在一线城市遇到过这样的病例。有段时间我到河南给当地的咨询师做督导,还能发现这样的个案。不同的地域,文化和道德观念变迁有一个时间差。
差不多在10年前,我开始发现来访者中有人格障碍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人格障碍不是重性精神病,通俗地说,它是一种性格上的缺陷,比如特别自恋,比如我们现在俗称的戏精表演人格,情绪非常不稳定,对亲密关系既渴望又恐惧,有自我伤害倾向,缺乏共情能力,缺乏同情心,还可能特别偏执。心理学上认为,一个人心理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基本的环境。很多时候人格障碍与早年的心理创伤有关。回去头去看,这些来访者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家庭结构逐渐瓦解。当人们享有更多选择自由,很多人选择放弃稳定的家庭生活,而不是去积极改善它,离婚率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中国有了一个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城市也有同样的情况:父母工作特别忙,孩子被全权委托给老一辈,或者干脆被寄养在祖辈家。所有这些东西都意味着,在成长环境中,这些孩子的亲密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剥夺的,这些都会对性格的养成产生影响。
这些年,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我有时候会感到一些来访者并没有特别大的痛苦,我也不认为我能给他们特别的帮助。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不需要再进行咨询了,但他们依然坚持把大量时间和金钱花在心理咨询上。究其原因,这些人是因为孤独而来,人们对亲密感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
我是“70后”,在我小的时候,社会相对来说是固化的。你从小到大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有发小,有朋友,一条街上的人都相互认识,知根知底。当人们有困扰的时候,有很多熟悉可信的人,可以给他们心理支持。“根”是什么?就是你熟悉的人,熟悉的环境。人类就是这样一种高级动物,你不可能随便找一个人去倾诉,你们的关系没到一定的程度,是不可能分享内心的感受和体验的。
今天的大城市,这样的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少。大量的人都是外来移民,“北漂”“上漂”。人们背负工作压力而缺少情感出口。一个独立的人,住在一个个小小的房子里面,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缺少朋友,没有倾诉者,没有亲密关系,这是一种自我监禁的状态。心理咨询实际上人为地创造了一个环境,提供了特殊的情感支持。它是职业的,它替你保守秘密;它是专业的,所以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和体验;它是平等的,你不用担心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受到否定和贬低。
我们时代的“无意义感”
人们对于心理咨询的需求,也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点:物质丰富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物质带给人们的满足感越来越小,人们精神层面的追求变得越来越迫切。但是悖论是:我们刚刚经历,并仍然停留在一个过度追求物质的时期,我们在精神层面上恰好是荒芜的。所以,我们要去努力发展、完善、满足人们对精神层面的需求,这正是时代进步的需要,国家发展的必然。
在这种荒芜中,近些年,我的来访者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他们颠覆了我过去的专业认知。
我在大学从事自杀危机干预工作。2010年的时候,我提出过一个“树理论”,如果一个人原生家庭有很多问题,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他容易出现抑郁或者绝望,甚至可能自杀。传统的心理治疗,无论是家庭治疗、精神动力治疗还是认知行为治疗,都有很多成熟的方法,可以去改变原生家庭对于个人的影响。但后来,我遇到了一个成绩非常优异的学生,进入大学第一个月就有自伤的行为,第四个月期末考试阶段就有尝试自杀的行为。给这位学生做危机干预的时候,我发现,和我以往所有的经验不同,我没有看到非常典型、非常明显的家庭问题,也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创伤经历。咨询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这位同学咨询的疗效和抗抑郁药治疗疗效都不明显,还是有明显的自杀倾向。因为他同时被诊断为抑郁症,所以我们将他送往精神科专科医院住院治疗。
当时,国内非常好的精神科专科医生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况应该很容易治疗,我们有非常好的药物。1997年大学毕业后,我曾经在精神病院工作,是一个有临床经验的精神科医生。我也曾经完全赞同这种看法。可是过了两个月,当我到医院去探望这个同学的时候,他的主治医生告诉我:“看来疗效不太明显,他现在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自杀倾向,其实不太有办法。”
这个孩子不得不休学回家。在这一期间,他仍在接受药物和心理治疗,但回到学校后,我发现他依然没有任何起色。最后,当这个孩子又一次尝试自杀后,只能退学回家了。我非常痛心,我相信以这个孩子的智力、性格、为人处事的情商,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但我们努力了4年,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
另一种路径
作为心理咨询师,我越来越感到,面对时代病和社会问题,心理咨询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它的作用是有限的。在美国,心理咨询这种医学模式被广泛推广,纳入商业医疗保险,但美国的精神心理疾病患病率却高达26.4%。面对大规模产生的心理问题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没有更好的解决路径?
2008年5月17日,我到汶川开始做灾后的危机干预工作。几千万人受灾,近10万人死亡和失踪,这样严重的创伤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你要怎么去治疗?坦率地说,我感到束手无策。面对这样庞大的受灾人群,当时全国大概只有33个人接受过完整系统的西方创伤治疗培训。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听不懂当地的方言。从汶川回来以后,我第一次参加了学校的校长办公会,汇报情况。我们和成都当地的大学合作,对方在重灾区彭州有一个校区尚建筑完好,我们在校区里建了心理咨询中心。然而,很少有当地来访者寻求帮助。大学、心理咨询、创伤干预,这些词都离当地人的生活太遥远了。我们主动去找灾民们交流,会发现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抑郁,什么是焦虑,我们根本不在一个话语体系里。心理咨询讲究“自助者,人助之”。灾民们没有这样的求助意识,他们甚至对这种帮助形式感到畏惧。
汶川大地震5周年的时候,《大河报》的一位记者采访我,我后来跟他一块儿去跟踪调研了10个失独家庭。我发现:绝大多数家庭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心理咨询或者心理治疗,但他们从创伤中恢复得相当不错。大地震8周年的时候,有一位失独母亲是所有人里情况最差的,依然有严重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她的家族里面,好几个孩子在地震中亡故。她住在都江堰,离成都不远。我为她联系了华西医院最好的精神科医生,四川大学最好的心理咨询师给她免费做咨询,她也同意了。可是事实上,她一次都没有去,怕远,怕麻烦。两年以后,我再去访谈时,却意外发现她的情况虽然谈不上痊愈,但已经没有了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也没有自杀倾向。究其原因,一是他们的居住环境更稳定了。国家提供了基本居住、生活保障,原来的邻里、亲属被安置在一起。这些人都有失去亲人的经历,有的人情况好点,有的人差点,大家抱团取暖,彼此拉扯。从前,这个妈妈总是在家里对着女儿的照片哭,后来人们硬是把她拉出来:打麻将,三缺一,少你一个不行。打打麻将,心情就好些了,这就是本土化的情绪调节。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一起去旅游,没钱去其他地方,在省内走走也好。这个接地气的社会支持系统可能比任何的心理咨询都要管用,而且低成本。
再者,对于失独家庭,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每对夫妇可以有两次免费做试管婴儿的机会。一些人如果能够重新有孩子,他们的情况会好很多,这叫生生不息。还有一些没能要上孩子的人,10周年的时候,他们开始跨入50岁,要考虑未来养老问题了。一个新政策是国家给他们发养老金,保障基本生活。有一个没有再要上孩子的失独家庭,夫妻两人办了养猪场,第一第二次都失败了。他们告诉我,第三次国家给他们专门批了一块免费的地,然后给他们办贷款,这一次,他们成功了。一方面我很赞叹人的韧性,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帮助,他们也不可能办成养猪场。
这些东西对于人们的心理康复都有最直接的作用,也都是心理医生没有办法做的。在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心理医生不解决现实问题,我恰恰觉得我们应该用专业知识去影响政策的制定。一个政策可以影响所有人,解决百分之七八十乃至九十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剩下来的少部分人,他们的问题才是医学模式去解决的。
在今天的中国,心理咨询的门槛很高,它要求来访者能够支付得起时间和金钱,还要具备相对来说很高的认知水平。但是心理健康不应该是这些人群的特权。最近一年,我参加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云南省临沧市做调研。在最基层,政府都在说,人们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很大,但没有专业人才去做这些事。我们需要培养心理咨询师去处理这些迫切存在的需要吗?很多时候,人们面临的是控制情绪失调、夫妻关系、子女养育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基础,不一定要进行专业长期的心理咨询,但它们又很重要,和人们的生活质量紧密相关。